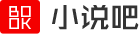谨以此文献给为诗歌曾经蒙难的已经离世了1离开
摘要:谨以此文献给为诗歌曾经蒙难的已经离世了1 年的鲁黎先生,以表达我对为汉语百年新诗做出过贡献的那些孤寂先辈和孤行吟者的深深敬意。 题记:谨以此文献给为诗歌曾经蒙难的已经离世了1 年的鲁黎先生,以表达我对为汉语百年新诗做出过贡献的那些孤寂先辈和孤行吟者的深深敬意。
——柏相
2012年10月12日下午4点06分,“络诗选”以《长风对一首诗的解析是否正确》为题,全文转载了一个叫长风的友的一篇博文,其题为《读初三语文课本上某首诗》。
长风的这篇博文,读的是七月派诗人鲁黎的《一个深夜的记忆》。长风在这篇博文中对鲁黎先生的这首诗肆意批评,几近于侮辱。说这首诗既“在所指上太清晰,在能指上被切割”,也“只能算是一时的情绪,既不能唤醒心灵,也不能带来美的意外”;同时,他还似乎有点愤愤不平地说:“就是今天,这样的作品仍然大行其道,并且以诗的名义。”
这个名为长风的博主,在其这篇读文的开头,不仅认为鲁黎《一个深夜的记忆》这首诗“显然是一首政治意味很浓的作品”,不仅极力宣扬“诗歌必然或显性或隐晦地涉及到政治,不存在要不要的问题”,不仅对鲁黎的这首《一个深夜的记忆》意见很大,腹诽甚深,并且对当下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简单罗列”了四点:一是“太急”,“急到死”,“不够从容”,“忘了写诗的过程”;二是“太精”,“多小聪明而无大智慧”;三是“太穷”,“穷到没有自我没有坚持,更缺少信仰”;四是“太脏”,“五千年的长发,都没有认真清洗过,里面长满了虱子”。
这个自诩“体育老师中诗写最好的、写诗人当中体育最好的”的长风,让我对“无知者无畏”这一句当代民谚,感受到了深深的敬畏;也让我对中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从事中国基础教育的某些言行失范的中学教师,产生了深深的隐忧。
鲁黎先生,1914年出生,原名许图地,福建同安人。他童年时随父母侨居越南,18岁时回国,同年在厦门发表他的处女作《母亲》。他22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4岁那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建国后,他历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天津分会主席等职,著有诗集《醒来的时候》、《时间的歌》、《天青集》。1955年,因为舒芜在《人民》的一篇发难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胡风先生自己递交给中央政治局长达 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贯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诗派”,被中央错划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先生入狱后不久,鲁黎与牛汉、曾卓等七月派许多骨干成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先后相继受到牵连,也都被打成了“反革命”,经过1978、1986、1988先后三次,才从政治、历史、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等所有方面,真正地获得了全面彻底的平反。
鲁黎先生是1999年离世的,今年是他逝世1 周年。鲁黎先生最初震撼中国诗坛的诗作是《延安组诗》,其实他真正的成名作或代表作,则应该是他受“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牵连,出狱后不久创作的新诗《泥土》。
《一个深夜的记忆》这首诗,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现被选入江苏教育出版社《语文》九年级上学期课本第15课,课文题目为《诗人谈诗》。
首先,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首政治意味很浓的作品,这只是一首诗,一首年轻诗人鲁黎在其早期创作的诗。它仅仅描写的是一个叫鲁黎的年轻诗人在一个深夜醒来时所看到的情景和随之引发的诗境联想。鲁黎的这首《一个深夜的记忆》,就跟李白的《静夜思》一样,只是诗人诗意栖居的某个瞬间的建构或纪录。
说这首诗是一首政治意味很浓的作品,这是对这首诗最大的曲解,也是对新诗艺术公然的别有用心的政治绑架。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也是一个很悲哀的预兆。
其次,这首诗并不像长风和一个叫阿亮的跟帖者所说的那么蹩脚。
针对这首诗,长风挑了三处毛病:
1、前三句:“从物到物,缺少提升,也就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可以说是一句散文被强行分成了三截。”
2、中间的三句:“不仅仅显得生硬”,而且“关键是作者情感的虚伪性,是假的,凭空捏造出来的,因此也无法打动人。”
、“最后两句”,也就是这首诗的结尾:“太过流俗”。
跟帖者阿亮,他明确反对长风将读诗和读政治关联在一起;同时,他也认为今天的诗歌,应该吸收一些散文和小说的长处。这两点我都赞同。
但是,针对这首诗,阿亮还认为:
1、前三句:“问题不在:从物到物,缺少提升,限制了读者的想象。也不在散文被强行分成了三截(今天的诗歌,吸收散文和小说的长处,是它的一大进步。鲁藜在那时能这样子写,赞一个!)。问题是以为是阳光,太假或不准确。以为是晨光还差不多。
2、中间三句:“月亮,属于夜晚的事物,和黎明应是敌对关系。月亮渴望黎明等于渴望自己消失。黎明的音响一点都不贴切,不是新奇是怪。是硬要和上句的弓弦硬配。”
、最后四句:“长风认为最出彩的两句我认为太流俗,惊喜度不够。后两句是想在结尾提升出意。可惜……!”
鲁黎先生的这首70多年前的旧作,真的有这么些毛病吗?我个人以为:不是这样。
首先,这首诗的前三句,诗中的“我”,把深夜流进门槛的“月光”以为是“阳光”,这很正常,或者说,这是“我”在诗境状态下的一种错觉或即时感受,明显的带有诗人的个性烙印。
这种诗境建构,不要说在新诗中,即便是在我国古诗中,也普遍存在并被汉语诗界大多数人认可。
比如,李白曾有诗句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如果按阿亮的理解,将“月光”比作“霜”岂不更假?鲁黎先生在诗中的“以为”,其实就等同于李白诗中的“疑是”。只不过,李白用的是比喻,而鲁黎用的是即时描摹。
李白把“月光”比作“霜”,不仅通过比喻描摹了乡思的“色”,也渲染了乡思的“冷”;而鲁黎把“月光”诗写为“阳光”,不仅通过即时描摹,诗写了带有个人独特体验的黎明或天亮的“色”,也反衬了自己对黎明或天亮的“渴望”。
至于长风所说的这三句“从物到物,缺少提升,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只能说明他艺术感受能力因为某种原因受限,不能说明这首诗的前三句的诗意建构有缺陷。
一首诗就如一片茶叶,要喝出那茶味,不仅需要足够滚烫的开水的浸泡,还需要喝茶的人有品茶的心境。喝不出茶味,很多时候并不是茶叶的问题。
我一直相信:一个真正的诗人,他能把白开水喝出茅台酒的味。
其次,阿亮和长风对这首诗的中间三句的品读理解,只能说明:阿亮有点像一个叫鹰之的人,“把诗当做科研来整”,用自然现象研究的那一套逻辑来品读新诗;而长风有点像与佛印对坐的苏轼,他是“以苏轼之心度佛印之境”。
鲁黎先生这首诗的中间三句,从“北边来”的“风”到“吹动了月亮的弓弦”,再到“听到了黎明的音响”,只是诗意建构的合理跳跃。这三句中最起码有四种主体性诗素的胶着:“风”、“月亮”、“我”、“黎明”。这四种主体诗素的诗意激发,不仅不“怪”不“硬”,而且几乎宛若天成,恰恰是鲁黎先生诗歌言语能力高过常人的佐证。
还别说,大家可以悉心回忆回忆,当今新诗诗坛,还能有多少人能在三句之内,用鲁黎先生同样的字数,把四种意象的个性诗意黏合并激发到这种程度?
如果说,鲁黎先生这首诗的前三句只是写景叙事超30亿元的15个和铺垫,那么,中间这三句就是在继续发散诗意并为这首诗最后的诗意提升做准备。如果非要说到中间这三句的情感,那就是中间这三句,是在前三句的基础之上,继续强化前三句中渗溢的那种对“天亮”的渴盼和对“黎明”的期冀。
无论长风也罢,阿亮也好,他们在批评这首诗的最后四句的时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这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候,都没有发现他们所读的那个版本,其实有一个明显的错误。
那就是,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其中的一个词语并不“最早”而是“最初”。我们似乎都应该要对自己的母语和诗作者表现出最基本的尊重。“最早醒来的人”和“最初醒来的人”,给阅读者的阅读感受是迥然不同的。
抛开他们的阅读文本自造或他引的错误,长风和阿亮对这首诗最后四句的理解,虽然也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但是,他们的“见仁见智”中,都明显带有对这一首诗的鄙夷情绪。我个人以为,很不应该。
虽然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无论是萝卜还是青菜,总都有可爱之处或可爱之因吧。
长风认为这首诗最后四句的前两句“有物有我,融合得比较好”,而最后两句“太过流俗”但他没有说为什么,只扔下了一句“不再赘述”;阿亮认为这首诗最后四句的前两句并没有长风说得那么出彩,而是“太流俗,惊喜度不够”,而且最“后两句是想在结尾提升出意”,也没有说得很具体。
我个人觉得,如果非要在这首诗中从“出彩”的角度找一两句出彩的句子,我认为很多。但是,如果非要从这首诗中找一个最能表达诗旨的句子,那恐怕就是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我感觉到万物还在沉睡/只有我是最初醒来的人”,或者最后一句:“只有我是最初醒来的人”,或者倒数第二句:“我感觉到万物还在沉睡”。
可以说,鲁黎先生的这首三节10行的诗,其他八句或者其他九句都是在为这最后的一两句所做的张本。
鲁黎先生这首诗的题目是《一个深夜的记忆》,这个题目的中心词或者说关键词是“记忆”。
在我读来,在那个属于鲁黎也属于东半球相当一部分人的深夜,诗中的“我”特别的孤单冷寂,一如《静夜思》诗境衬托下的李白。诗中的“我”和李白一样,也和李白不一样。
之所以说“我”和李白一样,是因为“我”既和李白一样在深夜里失眠,也和李白一样在静夜中孤冷。之所以说“我”和李白不一样,是因为李白是因为思乡失眠,而“我”可能是因为异族入侵山河破碎。
而诗中的这个“我”,你也完全可以把他读作就是为了诗歌或中国文艺曾经和一群人为中国文学遭受别有用心者残酷“整治”的鲁黎。
虽然它也许并算不上是中国百年新诗长廊中的经典,但在今时今日,在此时此刻,我显然特别喜欢鲁黎先生的这首《一个深夜的记忆》。
无论怎么样,李白的“静夜”和鲁黎的“深夜”,都给我们诗化了一个现实的困境,在这个困境中,我们失眠孤冷。这“静夜”和“深夜”,既是李白和鲁黎共同的现实困境下的无耐,也是所有处在这种困境中的人的温暖,直至今天,是他们的诗,还在依偎着感觉有点冷的我们。
千年前的李白和70多年前的鲁黎,似乎的确都是“最初醒来的人”,并且看着“沉睡的万物”,在一直醒着。
李白和鲁黎,这两个有着几乎一样世途遭遇的诗人,一个醒在唐朝,醒在“安能摧眉折腰”里,醒在异乡,醒在思念里;一个醒在异族入侵时期,醒在山河破碎里,醒在“万物沉睡里”,醒在被某些同族人嘲讽的悲哀里。
◆附:
◎一个深夜的记忆
文/鲁藜
月光流进门槛
我以为是阳光
开门,还是深夜
不久,有风从北边来
仿佛吹动了月亮的弓弦
于是我听到了黎明的音响
河岸被山影压着
有星流过旷野去
我感觉到万物还在沉睡
只有我是最初醒来的人
◆络诗选《长风对一首诗的解析是否正确》:
共 4261 字 1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文章以《一个深夜的记忆》作为解读对象,以批驳的方式作为解读技巧,揭示出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诗歌要不要触及政治的问题,这是作者引述的评论者观点和作者的观点都涉及的问题,虽然诗评没有纠缠这个问题,毕竟提出了一个值得作者和读者们思考的问题。怎样评价和看待一首诗的问题,是尊重客观的分析评价,还是义愤填膺地贬低?文章提出的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一首诗歌的解读问题,这是时评的重点,也是诗评的巧妙之处。作者采用批驳的方式解读诗歌,文章先引述了两位评论者对这首诗的评价,然后作者在赞同和反对这两人的观点中对该诗做了分析解读。这篇诗评给我们思考的东西很多,谢谢作者!【:春雨阳光】
1楼文友:201 - 1 : 8: 我从象征和非象征的角度解读这首诗,我从作者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角度解读这首诗,也抛开这些因素解读这首诗,都能读出其中的味道来。这首诗能引起争论,本身就说明这首诗值得品味。文学是不是完全脱离政治?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是今天的文学讨论最多的问题,值得思考。 语文教师
盐城治疗白癫风医院石家庄好的白癜风医院
必利劲好还是希爱力好
- 02-19[女生网]1980年长城币壹圆再以实力征服你,注意一字之差,价值差有钱!
- 01-13[女生网]千万不要随便穿著肉色的衣服…哈哈哈哈狠狠代入了!
- 12-28[女生网]应采儿带儿子出游,老大外表帅气招风耳惹眼,小儿子清秀似女孩
- 12-11[女生网]高油价“我家”?“三桶油”市值,一天蒸发近千亿!21天狂揽15板,这只股今天却跌停!芯片板块,逆势上
- 12-05[女生网]奥特维(688516.SH)子公司与合盛硅业(603260.SH)原为签订1.3亿元160型单晶炉买
- 11-30[女生网]孕七个月初产检“无胎心”,多和这些因素有关,孕妈可要注意防范!
- 11-28[女生网]后生初期|怀后生前三个月不能说?这是迷信还是另有说法?
- 11-21[女生网]过气方便面“东山再起”,强势到销量超过肯德基,网友:王者归来
- 11-20[女生网]Ulster霍尔大学优质课程推荐 BSc Nursing Science (Top-up) & MS
- 11-19[女生网]内蒙古民族大学22教育学考研复试线及考上解读
- 11-17[女生网]上海快递小哥骑行3公里为“燕子”送遗失的手机
- 11-16[女生网]越是穷,越不要觉得自己不行,先做好这3件大事,否则很难变有钱!
- 11-14[女生网]2022宁夏公务员考试笔试时间确认7月9日至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