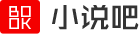我的五味人生17(1)
前言
大家好!我是一九五三年生人,71届下乡知识青年,一九七八年返城后经历了择偶、成家、求学、立业的生活关口,是“我们这一辈”人生旅途的亲身经历者和目击人。退休后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辽宁人民出版社非常重视。为此,该社解放以来,破天荒地出版了平头百姓个人的回忆录,使得我的《五味人生》得以问世。
从今天开始,《五味人生》回忆录将在每天晚上六点逐集发表在群里,全篇奉献给大家!
作者唐明达
我的五味人生
唐明达
一 偶遇初恋
阳春三月,大地虽然还没有解冻,可和煦的春风,暖融融的阳光还是让人格外地惬意。
八点多钟,刚刚退休的我,一身的轻松,兴致勃勃地逛着小河沿的早市儿。
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的眼睛不由得一亮!在一个菜摊前,一个身材标致女人的背影和她同卖家说话柔美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她?不可能。可当她回转头来,我怔住了!
是她......真是她?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她,竟然是我一别三十六年,一辈子想见又怕见的初恋情人—小提琴手吴晓迪!
更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她还如此的年轻,本应五十六岁的她,看起来竟然四十多岁的样子,仍不失美女的容颜。她高挑的个头,穿着得体的风衣,别致的盘头和她拿着蒜毫的纤细的手都是那样的美。
我们相视的一瞬间,她从我的目光里也一下子确认了我。那神情和我是一样的惊喜、又是一样的惶恐。此时,谁都想躲,谁又都不忍躲的眼神,还是交汇在了一起。
我径直地走过去和她不约而同地靠在了路边儿。
我轻轻地问了一句:“你家在这附近住吗?”
她的脸也是红红的,回道:“我家在大东副食南口。”
此时我的脸涨的很热,心突突地跳,脑子很乱。再往下,仍然是自己语无伦次的问话。
我不知问了些什么,也没听清她答了什么。
还是她结束了这尴尬的局面,微笑着伸出手说:“那你忙吧。”
我也伸出了手,只是轻轻地一握,让自己触到了一股强烈电流,似乎也感到了她剧烈的心跳。
她脚步匆匆地走了…
在自己的身边,闪过了一趟趟的摊床、掠过一波波的人群,直至走到小河沿公园西门的十字路口,也没寻到她的身影。
望着四面汇聚的人流,最后的希望淹没在浩荡的人海里…
我的心酸酸的、苦苦的。如烟的往事在眼前,像云雾一样的飘来浮去,自己被时间隧道拖回了那不堪回首的“青春”岁月。
二创作缘份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季,我在青年点儿已经渡过了六个春秋,为了不使自己的青春付诸东流,加之对文学的一点儿爱好,潜下心来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不平静的春天》
小说的内容是描写建点之初,在大队冯国珠书记麾下的一批知青,战天斗地,改造盐碱滩,当年开荒,当年受益的生活和事迹。并以右卫公社的一个坏分子黄国学混到欢喜岭青年连队,拉拢腐蚀知识青年的生活原型为副线,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资产阶级与,对知青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
我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小说的初稿,并分两个途径进行了投送。一是将书稿托南井子知青鲁东勇送到了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二是为了避免脱离基层组织之嫌,把复写的稿件,交到了东郭苇场宣传股。
没想到,那份复写的稿件送到东郭苇场宣传股后,正赶上盘山县的一次文艺汇演,我很快接到了参加县文化局文艺创作学习班的。
我是在食堂打饭时得到的,当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自己回到宿舍,从床头的木箱里掏出一件洗白了的仿军服,就匆匆上了路。
我坐马车,搭拖车,倒火车,几经辗转来到了盘山县城。
虽然浑身的汗水,一身的疲惫,可是看见了盘山县城的楼房和柏油马路,我还是感到格外的轻松和亲切。因为它让多年身处荒蛮之地的我,见到了城市的建筑,沈阳家乡的影子,我的眼睛一阵阵发热,心一阵阵发烫。
我一边贪婪的看着路边的影院、商店、工厂和机关,一边打听着的地点。在不大的县城里,我很快找到了报到处—盘山县第二招待所。
盘山县文化局把我们来自不同公社、机关单位、社会团体,一行二十多人的业余文艺创作者,安排到了盘山县第二招待所的一楼。
早晨还睡在青年点阴冷潮湿的房舍里,晚上居然躺在了洁净舒适的招待所,让我有了从没有过的愉悦的心情。
晚餐时更是让我兴奋不已,那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充满香味的餐厅里,靠南窗一侧的两张圆桌,坐满了文人。
自己进餐厅之后刚刚落座,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熘豆腐,油汪汪的馋人。要知道想吃这道菜,在青年点是绝对的奢望。尤其在冬季,知青一日三餐,顿顿吃的是大饼子、咸白菜汤,平日里见不着一丁点儿的油星,哪里能看得到油汪汪的豆腐呵!
稍许,服务员又端来了第二盘菜青椒炒肉,紧接着洋葱炒鸡蛋、韭菜炒干豆腐,一连竟上了十个菜,简直让我看直了眼。尤其是最后一盘子的红烧肉,让我的眼睛湿润了。
在那个年代,眼前这桌菜使我感觉好像是在梦中。真不敢相信,人间竟有这般美味佳肴,还有这样神仙般的口福享受。
说实在的,我真想一口吃了满桌子的菜。不要说我,那会儿任何一个知青都有包海的肚皮,长年累月的体力劳动,知青的饭量个个大的惊人。
我曾经创过一顿吃过十六个大饼子的连队纪录,后来被我的同床好友吴炳发以一顿十八个大饼子刷新了纪录。
餐桌上,也许别人过得都不是青年点的苦日子,各个的吃相有点装模做样。我只得耐着性子,守着规矩,直到人们都下了桌,才露出了知青的“本相”自己把第二碗饭,直接扣在了红烧肉的盘子里,吃的是毛干爪净,连油都没剩。
那年月家里穷得直到我中学毕业,就没看过七碟八碗的菜,从校门到青年点的苦日子,更让我没见过今天这般丰盛的席面,头一次接触的外界,真的让我开了眼界。
三初恋窗口
晚上就寝的时候,我的心情还在激动着,一时睡不着觉。突然有人轻轻地敲门,同屋的那位是高升农场的宣传干事,名字叫赵文革。他的床头正挨着门口,便顺手开了门。
只见一个梳着荷叶头的姑娘,站在门口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对不起,打扰了。我的蚊帐怎么也挂不上去,能帮帮忙吗?”
还没等我说话,赵文革已经笑呵呵地跟着姑娘出了屋。
这个姑娘给人的照面太美了,我没伸上手帮忙,觉得有几分失落。
姑娘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显得亭亭玉立。尤其她说话时露出的晶莹洁白的牙齿,还有那妩媚的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会儿功夫,赵文革回来了,自语道:“这美人儿就是尊贵,这都秋天了,还能有几个蚊子?”
我不无醋意地打趣道:“哎!老弟别得便宜卖乖,要走桃花运啦,嘿嘿!”
赵文革白了我一眼嗔道:“别瞎说,咱跟人家能运上嘛,那是营口文艺调演的第一把小提琴手!”
赵文革自甘暴弃的扫兴话,也泼了我一头冷水,让自己知道了姑来头,对姑娘一下断了念想。
第二天上午八点,盘山县第二次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开始了紧张的学习。首先是每个学员读自己的当家作品,是大家评议,提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最后由文化局专职创作的老师评定学员的作品。
在这个学习班,由于我带来的是中篇小说的稿本,并且受到了老师们较高的评价,而大部分学员都是写作歌词和诗歌的,所以大家对我格外地高看一眼。
晚间的时候,我的屋子里常常坐满了人。兴致勃勃的我也愿意给大家讲一些小时候的故事。这样一来,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我也越加讲得起劲儿。
最让我高兴的是漂亮的“小提琴手”也成了我的听众,后来几乎一天不落,而且来的很早。这让我更加来了情绪。自己常常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尤其是讲到高潮时,她的眼睛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每当我的眼睛扫向她时,她的面颊会刷的一下很红,我的脸庞会忽的一下很热......
这样的场景,让我好兴奋,好满足。因为开班以来,她始终不苟言笑,那种矜持,甚至让人不敢接近。不管怎样,这位“班花”也有注意到我的时候了,这就足够啦!
一天傍晚,我们创作培训班二十几人在招待所食堂吃过晚饭,陆陆续续地走出。
我的心里总觉得有种放不下的东西,不愿直接回到宿舍,身不由主地朝着小提琴手房间的走廊走去。
正巧,碰到了她和一个矮个女生刚从食堂回来。虽然我和小提琴手还没有正面说过话,但是,彼此在对方的心里已是“熟人”了,而且还知道她漂亮的名字—吴晓迪。
吴晓迪微笑地朝我点了下头,急忙扭过头去,慌乱地开着门,手里的钥匙怎么也对不上锁孔。
我已从侧面看见了她满脸的红晕,趁势搭讪地说道:“现在进屋很闷的,上外面散散风多好啊!”
“可以呀!”旁边的矮个女生叫小喇叭,名如其人,饶有兴趣地接道。
吴晓迪笑着瞅了我一眼,那表情好像看出了我的意图,倒让我红了脸,觉得自己的小图谋被人家看穿了似的。
我和两个女人走在大街上......繁华的街景让人目不暇接,小喇叭乐不可支地嚷道:“看看那楼,和我家的楼一样!唉,你们看,那边还有桥呢......”
此时的我,走在两个女人的后面。自己的耳朵虽然听见了楼啊桥的,可是目光却落在了吴晓迪的身上。她穿着当时最时兴的女士军装,背影的掐腰曲线恰到好处,显得人整个的身条格外地打眼。
吴晓迪走在前面,眼睛的余光也在扫着后面的我。
小喇叭激动了半天,说了好多的话,见我和吴晓迪没有动静,突然发觉了什么似的,说道:“我上前面看大桥去喽!”
看着小喇叭远去的背影,再看身边回头朝我微笑的小提琴手,自己到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不知怎样开场白了。
吴晓迪笑着开了口:“唐老师,听说你们青年点儿出芦苇是吗?”
“是的!”我急忙回道“我们东郭苇场的苇田是世界第二大的”
“你们一定很骄傲的?”吴晓迪看着我
“当然,选集用的纸都是我们的芦苇造的。”芦苇的话题,不免让我有些神气。
“看把你骄傲的,你愿意在那扎根吗?”吴晓迪认真地问我。
“不扎根咋办?六十年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就得听从党的安排。”我回答的有点装腔作势。
吴晓迪听后没有接我的话茬,不再说话。
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吴晓迪:“难到你不想在农村扎根吗?”
“不想,我不想对着没有观众的农村大地拉小提琴。”吴晓迪的眉宇锁了起来,说:“唐老师你也不应该把根扎在这里,你的中篇小说写的那么好,应该回到城市当个作家。”
听到吴晓迪的话,自己好像在听童话。不过我看出这个姑娘心气儿,不是一般的高,从内心还是很佩服人家的。
那天我们不知不觉聊得很晚,直到夜幕降临,小喇叭回来了冲我们做了个鬼脸儿,这才感觉到应该回到宿舍了。
四瓜熟蒂落
随着创作学习班的进程,我和吴晓迪的接触逐渐增多,来往自然频繁起来。
一天下午一点钟,我刚刚睡醒,吴晓迪拿着一个封面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红色日记本,来到了我的房间,不好意思地说:“唐老师,我有篇日记想写好,却怎么也写不好,麻烦你给看看行吗?”
看她难为情的样子,我赶紧让开了床头,请她落座,忙不叠地给她倒了一杯水,接过了她的日记本。
我翻看后,原来是她不久参加营口市文艺调演,获得小提琴比赛第一名的一篇日记。几页纸上写得密密麻麻的,足有一千多字,看出来是下了不小的功夫。日记里写的主要是她比赛前的心情和获奖后的激动。
我让她讲诉述一遍那天比赛的情况,听后我当场作了修改。我把笔触主要放在了描写比赛的场景上,写出了比赛场上人们屏住呼吸,静态的紧张气氛,和表演后人们赞许掌声,动态的热烈场面。
她看完后竟激动地捧着我改写的手稿,兴奋地说:“唐老师,你给了这篇日记点睛之笔呀!”
那场景我自然高兴,这让吴晓迪和我又拉近了距离。
再后来几次去餐厅吃饭,吴晓迪都会在旁边的座位放一个物件等我的到来,又自然多了许多亲近的话语。这份殊荣让我很兴奋,一连几天夜里难以入眠,白天更是魂不守舍。尤其是每天早上洗漱的时候,我都会在走廊里,远远地看着她。
那会儿,小提琴手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她姣好的容貌,就连她的形体,坐姿和步态都是那样的美。尤其是她的行走,无论脚步走得快与慢,还是双臂摆动的大与小,肩头都是平稳前行,犹如玉树临风。她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偶像在心中的感觉。
由于我来学习班时走得急,没带足够的钱和粮票,在文化局经办处挂着帐。那时我们每个学员每天要交四毛钱、半斤粮票的伙食费。在学习班临近结束的时候,我拿着家里寄来的钱和粮票,到经办处去补交所欠的伙食费。
收费窗口推出了我的钱和粮票,飘出了话语:“吴晓迪已经替你交完了。”
什么?吴晓迪替我交了伙食费?我呆住了。
收款员看见我狐疑的样子,诡秘地笑了。
这让我联想起和她近来一段的接触,深信她对自己产生了情感,心中禁不住涌起一股莫名的暖流。
那年月谁家的日子都不宽绰,那个人手里的零钱都不多,我的食宿费怎好让人家姑娘交钱呢?我急匆匆来到吴晓迪的寝室,想把钱交付与她,没想到一屋子的人正在说笑。
小喇叭拿着一个红红的大苹果冲吴晓迪取笑地嚷嚷着:“晓迪,多好的苹果,这么多天不吃,咱们帮你吃了吧!哈哈!”
吴晓迪急着抢回了苹果,回道“谁也不许吃”
小喇叭笑嘻嘻地抢白道:“是给作家吃的吧?”
几个女生也跟着哄笑着......
屋里的人见我推门进屋,笑得更厉害啦。吴晓迪却把目光闪在了一边,唰地红了脸,比苹果还红。我见势不妙,装作不知,随意拿走桌上的水壶,赶紧退出了屋。
一连几天我总想找机会把吴晓迪替我交付的钱款,郑重地还给人家,表示内心的谢意。可是有几次照面的机会,吴晓迪都躲着我走开了,而且走得很急。
我远远地望着走开的姑娘,心里苦道:“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不过每次我都会久久地望着她,因为每次走远的时候,她都会回头看我一眼。
我的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先是苦苦的、继而酸酸的,转而又甜甜的......一种莫名的情感,让我渐渐打开了爱的窗口,姑娘虽然走远,却已经进了自己的心房。
满脸通红的小提琴手上了车,随着拖车的开动,她不停地向我招着手,喊着、说着…
拖拉机的轰鸣,淹没了她发出的语声。但是她不住地点头,不舍的目光已经告诉我:她接受了我的爱情。
五昙花闪落
拉着小提琴手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走了,直到卷起的尘烟淹没了她的身影,我这才收回目光,想起她塞进我兜里的东西,掏出一看,正是那天她从小喇叭手里抢回的苹果,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和吴晓迪分开后,真是相隔一日如同三秋,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满脑子都是姑影子。想得最厉害的时候,自己会跑到几里以外的大窑桥上呼喊一阵子,默默地回到宿舍,把脸紧紧地贴在创作学习班结束后集体合影的照片上,流下初恋苦痛的泪水......
回到青年点第九天的中午,连队的拉水车从大队,给我捎来一封来自台安县古城镇公社胜利大队的信件。娟秀的字迹一看就是出自女人的酥手。自己用发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心怦怦地猛跳,脸阵阵地发热,不知信里装的是怎样的一番柔情蜜意。
打开信瓤,看到的只是八个字:“见信速来,车站接你”再下面是古城公社胜利大队的电话号码。我眼前不由的浮现出她焦急期盼的让人心疼的娇嫩面孔。
我急火火地跑到连部找带青老农请假,张宝成不到五十岁的年纪,眼角堆积的皱纹几乎遮住了眼球。他知道我请假看病是假,可无凭证,我又是老青年,只得不耐烦地说道:“看病回来,把诊断书交到连部。”
我见到一处自来水管,走了过去。自己本来在连队已洗过脸,还是又洗了几把,生怕脸在路上落了灰,在心爱的姑娘面前丢分。自己还在供销社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买了一条图案别致的白纱巾。
还好赶上了准点儿的火车,并找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我陶醉地看着窗外的景物,想着见到她的情景。那真是天也美呀、地也美呀、水也美呀,其实主要是心里特别地美!
十一点半,火车到了拉拉屯车站。我急不可耐地挤下了火车,一眼就看到站牌底下的小提琴手。她身披一件灰色的风衣,微风撩起的秀发,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我大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吴晓迪,她微笑地向我走来。
可走到近前,她的笑让我觉得不太得劲儿,那是客气的笑,有分寸的笑。走出站台,她要领我到附近的饭馆吃饭,自己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说:“不忙吃饭,不忙吃饭!”
我顺从地跟她走了一段路,她的头始终偏着。再仔细瞧,她哭了。
我急了,搬过她的头,只见她满眼的泪水......
她默默地领我走出站台,在一棵榆树底下停住了脚。一群麻雀好像感觉到树下,一对男女会发生不快似的,呼啦啦飞的一个不剩。几分钟的沉静,相互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 。
她终于开口了,原来她从盘山回来,就把恋爱的事告诉了家里。她的父亲是沈阳一家大型国企的革委会主任,比盘山县县长官还大。她父亲派人专门到我父亲单位做了政审,调查出我家的地主成分,父亲是宪兵的历史问题。
这让她的父亲如临大敌,似遭天塌大祸,连夜坐吉普车来到女儿的青年点兴师问罪,劈头问了女儿几个问题:你对个人问题如此草率,参军的怎么办?做政工的母亲怎么办?父亲还能不能在领导位置上干?那小子会有什么前途?你和他以后怎样生活?
这一连串的政治影响和前途问题,在那个年代,莫说是个女孩子,就是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也会败下阵来,她终于缴械投降了。
听完她这样的陈述,面对眼前一个个的现实问题,我深深低下了头。此时我知道,任何的理由和解释都是苍白的,任何的挽救和坚持都是无力的。
我把泪水往肚里咽了咽,没有让她送别,也忘了和她握别。自己静静地走回了车站,再回头看那棵老榆树时,已没了她的身影儿。
这时我才感觉到浑身像抽了筋、断了骨一样,迈着沉重的脚步,顺着铁轨毫无目的走了下去......
六噩梦不醒
夕阳西下,已近黄昏。不知走过了几个车站, 也不知路过了多少村庄。我终于撑不住身子,迈不动步了,一瘫坐在一个土丘上,顺势躺在了草丛里。
仰望着头上掠过的一朵朵无情的白云,忍受着荒野袭来的阵阵冷风。几个蚂蚁讨厌地在我的身上窜来窜去,后来竟事无忌惮地爬到我的脸上,全然没有感觉,任由蚂蚁的欺负,自己成了天底下最渺小的生灵。
是啊,怎能不自卑呢?家庭的地主成分,父亲的历史问题,像挡在我前面的两座大山,让我无处可逃,无路可走。
记得小学时入红小兵,中学时参加,自己都要受到了歧视和排挤。放学回家的时候,和同学合不了帮,课外游戏时,与同学如不了伙。更甚的是,遭到了个别同学的欺负时,如果还嘴,就会遭致地主翻天了的骂名。我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这样倒霉的家庭?更不明白自己生下来是的子女?
毕业下乡了,虽然没有了明面的欺辱,但也是知青连队弱势群体里的被歧视者。不久前,上面到青年点儿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和连队的同学一样报考,一起参加了在欢喜岭小学的面试和笔试,而且有幸获得了东郭苇场第二名的分数。苇场招待所所长在场部亲眼目睹了我的大学录取书。
这个所长是我几次上苇场宣传股送作品相识的,和他很谈得来,成了至交。他很快托人告诉了我,这个足以改变命运的喜信儿,可是最后却没了、没了下文。
我急切地找到了苇场的张朝臣书记问个究竟。
张书记回答的非常直率:主要是家庭成分的问题,上工农兵大学不同于招工,需要政审。
我鄂然,“党的政策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
张书记不耐烦了:“那你的政治表现在哪里?”
我理直气壮地回道:“我被评过大队先进知识青年啊!”
张书记笑了说:“那是你应该做的,是组织给你的荣誉,不要有了成绩就翘尾巴嘛!”
我哑然,招生对我成了无言的结局。
我想起了赖以生存的连队,又是我生活的一堵墙。为了扭转当时青年连队普遍出现的混乱局面,自己曾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对知青工作的七条批评意见、九条建设性意见。分厂领导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对知青工作很有新意,逐级上报,最后到了盘锦地区。
由于我的“意见”在当时知青的大环境中,不仅切中时弊,揭露了普遍问题,还提出了其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因而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县里很快发文,组织各级代青学习。这样的事态发展,是我和连队领导始料未及的。
连队领导没有从大局出发,从正面去理解、去认识。反而认为我是隔着锅台上炕,在太岁头上动土,触动了顶头上司的尊严。
带青老农连队王贵福大怒不止,在连队和大队几次忿言:“招工谁走,唐明达不能走,唐明达必须把青年点改造好”
领导说话是算数的。果真,长年不上工,在家泡病号,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青年儿都回城了,我却在多次招工中一动不能动。
细细想来,眼前的唐明达真是前无出路,后无退路。今天又因家庭问题被女人弃之荒野,婚配都成了问题,日后何以成家立业?简直没有了活路啊!
凄凄然,我闭上了双眼,无助的泪水湿满了衣襟,脱口喊出:“爸爸、妈妈,儿无能,儿无用,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啊!”
“咕咕.....咕咕.....,”耳边突然传来水鸟的叫声,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这才发现铁道路基下面是一片大水塘,在晚霞的映衬下,泛动着金红色的波纹,美极了!
蓦然觉得这才是我的去处,多好的归宿啊!脑子产生了奇异的幻觉:我在水塘里洗礼,披着金色的彩带,飞上了天空,超脱了尘世,进入了天堂......
人大凡自杀绝命之前,应该是都有这番美好幻觉的召唤,才义无反顾走上不归路的吧。
我径直地朝着水塘扑去.......
七 明人指路
我向水塘跨出去的腿,还没落脚,自己的左臂,突然被一只大手抓住了。
我猛然回头,见是一位穿着铁路服五十岁上下年纪的人,扯着嗓子喊道:“孩子别想不开呀!”
我惊讶地看着他,惶恐地挣脱着…
“别怕,我是铁路道班儿的,我瞅你有一袋烟的功夫啦。”来人不由分说,把我拽出了水塘。“孩子说吧,有什么难事儿?看看大叔是不是能帮上忙?”老人一脸的着急。
看着他慈祥的面孔,我想起了惦记我的父亲,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他摘下脖子上的手巾,用他粗糙的大手,爱抚的给我擦着不断流下来的泪珠。
我一肚子的冤屈,一腔的苦水像开了闸似的,向老人全部倒了出来。
大叔听了我痛苦的经历,艰难的处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圈开始有些泛红。他拿出烟口袋,卷了一颗烟先递给了我,自己忙谢说不会抽。他劝道:“抽口不碍事儿,人生啥滋味儿都得尝尝。”
说话间,他又卷了一颗烟,点燃后,狠狠地抽了一口,一本正经地说道:“小子,听你刚才喊,你是无用无能的儿。错了!你大学的分数必竟考上了,那么好的姑娘终归喜欢过你。说明啥?你小子行!大学,有多少人不敢考啊,那么好的姑娘,她看不上的人多了。你比那些人要强吧!他们能活,你为啥不能活?”老人说得很认真。
他见我点了头,又说:“说是没去上大学,和姑娘到不了一起,那不是你本身的错,是缘没来,命没到。”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加重了语气:“凡事都有个时来运转,气候还有个春夏秋冬,太阳也不可能总可一面照呀!你才二十多岁,这才哪到哪呀!”
老人连珠炮似的话语字字有声,句句在理。自己的心头,好像被他打开了一扇窗户,透亮多啦。
老人转过身来指着水塘又说:“开春的事儿,这里死了个人,想不开投的水。咋了,死了就死了,啥都完啦!你呢,活着呢。喘气就有机会,活着就有奔头。”说着他又使劲掐了下我的肩头,非常自信地说:“别看我是个工人,可我书看的不少,眼不拙。大叔看准你了,就凭你小子的长相,你的文化,准有出头那天!”
老人的话,让我佩服得不住地点着头。
看着天色已晚,老人突然:“还没吃饭吧?”
说真的,从早晨就没吃饭,这会儿已经饥肠辘辘,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我毫不掩饰地冲老人点了点头儿。
老人二话没说,拽着我的手就朝着前边不远的车站走。
到车站进了一间屋子,老人打开了一个柜门,拿出一个饭盒递给了我。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窝头和几根儿剥了皮的小葱儿。
老人可能出去打水去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一会儿的功夫,老人拿着一个大茶缸子和一碟酱回来了,见状忙说:“这还有酱呢。”
他来到我身边一看,葱已经没了,窝头儿还有一口,只得苦笑了下,递给我一杯水。我接过水杯,一扬脖下去了。
接着老人又打电话,给我联系了一列马上开往锦州,恰好在石山有站的货车,这下自己还省了火车票钱。
上车时我对老人连连鞠躬,千恩万谢。老人还不放心地嘱咐我:“大丈夫何患无妻,忘了那个丫头吧!”
火车开动了,我掏纸想擦一下工具箱落座,顺手掏出了给小提琴手买的白纱巾…..。
还有什么用呢。自己来到车门口一扬手,白纱巾飞出了车外。
老人看见了飘走的白纱巾,会心地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此刻,列车已经开动,驶向了石山车站,我连夜赶回了欢喜岭青年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