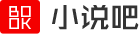这样的文学场面久违而陌生
通过文学作品,通过侯孝贤的电影,通过那个关于台湾“朱家三姐妹”的传奇故事,台湾地区作家朱天文在大陆读者那里几乎成了一个神话般的“符号”。20年来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朱天文,前天晚间做客东方早报文化讲堂,以“文学与电影”的名义,与早报读者面对面交流。同乐坊芷江梦工场首次在开场前一小时便涌满了读者,以致提前半小时来的读者只能席地而坐,现场气氛真诚而热烈——连朱天文也说,“这样的文学场面已经久违了,反而显得有些奇怪和陌生,像是参加一个摇滚巨星的聚会。”这样的场景让朱天文回想起了1970年代末办杂志的年代,“在台湾,文学已经濒临绝种了,那是一个寂寞的事情。”
相对于其他台湾作家,朱天文是一个更纯粹的小说家,她极少涉足政治和公共讨论,而在她自己看来,小说家的角色就像一个收尸人,在社会洪流之后保留历史和个人的记忆。
谈如何进入电影圈
“这是一个机缘”
关于电影,我们(注:指朱天文和侯孝贤)就是各自一片天,谁也别想听谁的。那为什么又会在一起合作?我想这是一个机缘。在进入电影圈之前,我写小说,办杂志,办出版社,和电影没有关系。后来我的一篇小说(《小毕的故事》)登在报纸上,他们看到了这个故事,就买这个版权。当时在台湾电影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分子是不看台湾电影的,觉得“国产片”非常没水准,只看好莱坞和欧洲电影。当时的台湾电影,要么是琼瑶电影,不然就是黑社会商业电影,跟生活完全没关系,相反台湾文学大概比电影早十年。侯孝贤他们做了十年学徒上来,他们开始想要改变,这个时候看到这篇小说,就想从文学改编成电影,这好像是一个接口。
侯孝贤是编剧出身,他不大需要一个人替他编剧的,那他为什么要找我们这样从来没编过剧的人去帮他?他要的是什么东西?事实上第一次写了剧本交给他以后,他大概只用了其中一句话,其他的全部改了,而且是一边拍一边改。所以,当时我觉得,“那你为什么要找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呢?”当时侯孝贤说了一句话,“我想要有一些意外,要有一些空气进来,因为我做了十年的电影,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公式化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一个根本没有写过剧本的人,不按照你的那个章法来做。”《小毕的故事》是一个卡司(明星)都没有,大部分是用非演员,但非常卖座。大家一看到这个电影就说,在影像上,第一次看到说人话,有一种亲切感。《小毕的故事》第一次框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让大家看见自己。紧接着在台湾就是跟风,改编一大堆的文学作品,包括黄春明、白先勇等等。
大量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文学的素质就加到电影里面去,也丰富了电影。在一个世界的电影版图上,有欧洲电影、好莱坞电影,我觉得台湾地区电影在当时的电影版图上贡献了这么一块——它的写实美学,我就参与了这块拼图。你看见一个事情从没有可能到有可能,从无到有,这对我是一次人生非常大的经验。
谈如何与侯孝贤合作
“我是陪他‘打球’”
后来越来越清楚,文字跟影像是两件事情,根本是两件不同的容器,装的东西也不一样。电影不是靠对白在推动,真的就是一个用影像在讲故事,用影像在推动世界。当你理解这个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心平气和。[NextPage]
对我来说,我的领域根本不在电影,我的领域是在文字上面。所以我会非常大方地讲出来,电影不是编剧的,电影是导演的。像侯孝贤属于作者式的导演,你不可能写了一个剧本给他说,“我来执行这个剧本”——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是一个发球者,一个发动者,我所能贡献的,不是作为一个编剧,我是作为一个他的对手,陪他“打球”;我的第二个贡献就是,不断地扔各种书给他看,我只要一看到一本好书就扔给他看。他的好多电影,就是我扔书给他看,拍出来的。他拍《郑成功》的时候,要拍秦淮河 生活,我就扔给侯导《海上花列传》,他后来毫无困难地看完,看完以后拍了电影《海上花》,这就是我的贡献。
我之所以不跟其他的导演合作是因为“频率”太不同,“频率”太不同的时候,你要在这个过程里头花很大的力气先把“频率”调到一起,这样我还做电影干什么?对电影我是没有野心,也毫无斗志。因为电影是导演的,不是编剧的。
我写电影剧本是我的谋生工具了,基本上就是一年或者两年,有时候三年写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可以来养活你的小说,因为生活很简单,花费又不多,就可以养你的小说。而小说是你的武器,作为你立足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媒介。
侯孝贤正在计划中的电影《聂隐娘》是讲一个女杀手,最终却杀不了人的故事。整个电影就是讲她,为什么杀不了人。剧本的第一部已经做好,大概9月会先拍,因为日本演员妻夫木聪的档期是9月份,9月份会先拍他的那一部分。
谈作家角色和写作
“小说家像收尸人”
我觉得文学还是蛮有用的。我自己写小说的,其实某方面来讲,小说真的是不能做什么。我觉得某方面来讲,小说家就像一个收尸人,一个战争过去了,坦克过去了,大家都走了,那谁来清理这个战场?我觉得这时候是小说家出来。当社会滔滔往前去的时候,不断地留下东西,不断地抛下东西,这个时候那些所谓的收尸人,他开始来收尸,一个个捡,帮他们清洗,帮他们保存,帮他们记录,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说家做的事情。我只做我能做的部分。
我写小说已经20多年,一开始写小说,从熟悉的事情写,都有一种半自传式,慢慢地可以有你想象、虚构的部分,但是都不是凭空来,都是从现实观察出来的。可是因为你的历练够,就有你可以飞翔的部分,你可以想象。另外,当你决定要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田野调查。就是把一个领域的东西,整个埋头进去。所以决定要写这个题材(《荒人手记》)的时候,做田野调查是结结实实泡在里头泡了一阵子,泡到要发芽了。当时有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事情没有办法对人讲,只能对我一个人讲,我变成了像《花样年华》里头的树洞。原先我是如此的冷漠,如此不关心这一块,当你明白了之后,你有一种不平之气,你想把不平写出来,让多一点的人理解。作为一个小说家,只不过是在做一个事情,把原来可能铁板一块的东西,去松一下,去描述它,理解它,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就像一个蚯蚓把(土地)松动了。
(:郭婧涵)
弥勒灯盏花药业简介
弥勒灯盏花药业在哪里
弥勒灯盏花药业发展
肾阴虚会引起哪些病利鲁唑片能延长多久
传说中的八子是啥
- 12-29[武侠]布里奇斯季后赛单场据估计30分&4三分&4帽 历史第7人&比肩詹杜科
- 11-14[武侠]Alessandra Rich 2022早秋系列,修身廓形的韵味,亮点更添时髦
- 11-11[武侠]率先8个风华音乐大师工作室落户宁波大学
- 10-27[武侠]地球磁场缓慢移动,磁场强度下降10%,地球或将已是下一颗火星?
- 10-22[武侠]投资者提问:二季度制造任务紧张吗?有什么技术上的新突破吗?
- 10-17[武侠]曾年销30亿的“神酒”江小白,为何如今无人问津?假象原因太现实
- 10-03[武侠]近一个月股价跌近50%,傲农生物:4月份起生猪出货头均毛利较一季度已明显改善
- 10-02[武侠]新纪元古玩艺术品在线模拟器:精品推荐——佳品磁铁陨石
- 09-30[武侠]西安旅游职业中专研议陕西省高水平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名
- 09-28[武侠]又挖多特?哈兰德3月曾接触拜仁 双方拜访一个小时
- 09-07[武侠]长春视觉艺术生文化课英语学习方法,高三学校分享
- 08-27[武侠]微软大受欢迎《壮志凌云 2:独行侠》联名款 Xbox Series S 主机
- 08-10[武侠]蔬菜中蕴含的中医知性:芹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