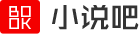父亲三章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游行
一九一九年初春,乍暖还寒,背阴的屋檐上还挂着尚未来得及融化的冰锥。这一天的早上,太阳还在云堆里挣扎,在济南天地坛东源盛酱菜铺当学徒的父亲,正在用他那双被酱菜缸群里的盐水泡得又红又肿、裂了许多口子,一戳就出脓血的小手,吃力地把一大罐酱油倒进那个个头跟他差不多高矮的咸菜缸里面的时候,忽然听到从大门外边传来一阵阵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及由远而近的脚步杂沓的跑动声。
当时,父亲不知道外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来不及跟身边的徒工柱子打声招呼,便 嗵 地丢下罐子,拔腿就朝门外跑去。
父亲跑到大街上,嚯,只见马路中央黑压压涌来了一片人潮。这些人,打着小旗子,身穿学生装,有男、也有女,一路由东向西潮水般涌来。他们高呼口号,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样子,让小小年纪的父亲,不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与此同时,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也早已聚集着大批观望的人。他们怀着同情,敬佩,惶惑不安,甚或恐惧的复杂心情,目睹着马路中间这支潮水般的游行示威者的队伍。
父亲夹在人群中间,听身旁的大人议论了半天,终于弄明白了。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合会开会处理战后事务,因胶济铁路被日寇强占,我国全国学生大罢课,及商店罢市,以示坚决反对。这些学生,就是来自齐鲁大学和济南师范院校的爱国青年。
就在这时候,父亲忽然看到,又有一波游行队伍走过来了。走在这波游行队伍最前边的,是一个如瀑长发里束着一条白丝带的年轻女生,她身穿月白上衣,深蓝裙子,由于一路振臂高呼口号,女生的嗓子已经喊得嘶哑了,晶亮的额上还闪着汗珠。
学生们的爱国举动,极大地激发了父亲的爱国热情。当时,年仅15岁的父亲,望着那个高挑身材的漂亮女生一路走来,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他拽着身边柱子的手,说了句,柱子,走!两个小孩子,就果敢地随路边不断融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的人们,也迅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去了。父亲举着小旗,也高呼口号:
打倒日本侵略者!
还我主权!还我胶济铁路!
抵制日货!爱国无罪!
以后的几天里,每天上午,父亲总要擓着一个大竹篮子,一个小竹篮子。大竹篮子里面盛的是东源盛酱菜铺高老板给学生们蒸的热馒头,小竹篮子里面盛的是东源盛酱菜铺高老板给学生们做的两菜一汤。这几天,学生联合示威游行,抵制日货的大运动,也惊动了东源盛酱菜店的高老板。高老板指命老板娘孙氏每天中午给学生蒸几屉馒头,做几个小菜,也算聊表自己的一份爱国之心,让做徒工的父亲给学生们送去。
父亲每天要走过两条马路,到工商会去。在那儿,父亲是随工商界组织的送饭队伍,一块赶到省政府所在地。这几天,省府驻地坐着成千上万的学生,学生们堵塞了交通,行人和车辆也都纷纷停在那里,驻足不前。太阳晒在学生们的脸上,他们面无表情,集体静坐示威。打出的横幅和标语上写着: 还我胶济铁路! 要主权,不要侵略!
可是,叫父亲弄不明白的是,饭送来了,水也送来了,那些大学生们却连看也不看一眼,仍然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无动于衷。
父亲知道,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已经坐在这儿持续了四五天时间了,有些体质较弱的学生,已经渐渐支撑不住,饿昏在大街上了。
父亲问高老板,高老板说,学生们不吃饭,是为了给当局施加压力。
可是,随后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却叫父亲遇到了麻烦。
市盐政这些年一直供应着东源盛酱菜铺的买卖用盐,是高老板的买卖靠山。市盐政的马主管,是高老板的桓台同乡,东源盛每年的进货盐价,都是按特殊关系照顾的。因此,高老板每年的中秋、春节,都要给马主管送礼不少的。
这天,市盐政的火夫王大胡子,忽然给东源盛来了,说要两桶酱瓜,三桶腌黄瓜。快点送来。
放下,高老板马上调集货源。然而,高老板在去找送货人时,这才发现,派去给学生送饭的父亲,到现在居然还没回来!
市盐政的王大胡子,是个土匪出身,脾气暴躁,张嘴就骂人。他自恃在政府部门做事,狗仗人势,气焰嚣张。王大胡子眼看着天已过晌,咸菜居然还迟迟不见送来,便勃然大怒。他又摸起,在里破口大骂高老板不识抬举,竟敢怠慢公务,并威胁说从此不但再不供应盐货,而且马上就派人去砸店!
高老板放下,战战兢兢,赶紧来到院子里,叫上柱子,亲自蹬着三轮,将货送到盐政大楼。高老板是个贫苦出身,老爹从上辈子就跑到济南府打拼,好不容易置下了这份家业,赢得了金子牌的名声。高老板深恐父子两代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买卖,眨眼间就变成一片狼籍。当然了,高老板也知道,虽然说这王大胡子在市盐政不过是一介鲁莽火夫,他发火归发火,也不一定就有这么大权力,真敢来砸店。但是,酱菜毕竟是市盐政要的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盐政老爷啊。高老板就劝自己,东源盛几十年来一直吃着他马主管的廉价盐,一旦真断了这廉价盐的供应,东源盛岂不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得,君子不跟牛治气,不跟这鸟人一般见识,赶紧送货去!
高老板见了王大胡子,先拉他到一边,悄悄塞上二百吊钱,给王大胡子一再作揖,谢罪,最后才算了了事。
从市盐政回来,一向胆小怕事、今天又亲劳自己蹬着三轮去给王大胡子服小作低送酱菜,并无端地又赔进他二百吊钱的东源盛大掌柜高老板,越想越生气,车走到半路,他先支柱子蹬车回店铺,自己却折到了院东大街恒庆昌银号,气势汹汹地找到父亲的举荐人族大爷李守芳,给他告了父亲的状。高老板的态度很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竟然当场就把给他惹了事端的父亲解雇了。
李守芳是我的一个本族大爷,当时是在济南院东大街恒庆昌银号任副经理。当年,族大爷是应我乡下的爷爷的恳请,把当时年仅15岁的父亲,从章丘老家带到济南当学徒的。族大爷平日煞是尊敬我爷爷,他和我爷爷一样,原本也是想教乡下的父亲,摆脱贫困,在省城闯出一番事业的。没想到,父亲出来才几天,竟然闯了祸!
族大爷把父亲叫到恒庆昌银号,狠狠骂了父亲一顿。族大爷骂父亲不懂事,说你一个小学徒腌你的咸菜啊,跑到大街上游什么行!现在时局动乱,混碗饭吃容易吗?族大爷吓唬父亲说,把你抓到局子里,看谁管你!父亲吓哭了。父亲知道自己闯了祸,族大爷骂得有道理。可是,父亲仍然想不通,如果胶济铁路要不回来,仍然让日本人霸占着,那多丢中国人的脸啊?父亲认为,当局软弱无能,如果大家也都不站出来,那中国人不就更叫人瞧不起了吗?父亲想,高老板是爱国的,他解雇了自己,是为了他的生意。父亲因此也不恨他,高老板毕竟也要生存啊。只是那个土匪大师傅太胀胞,欺人太甚,准不得好死!
可是,叫父亲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族大爷这回却真生了他的气,族大爷拍着桌子叫父亲滚!叫父亲立即离开济南,重新回到老家章丘种地去!
父亲害怕极了。父亲知道,族大爷在济南是个脸面人物,要强,他或许认为,经他推荐的徒工,竟然给朋友惹了祸,就等于丢了他的人。因此,当时,不管父亲怎么痛哭流涕地求饶,认错,倔强的族大爷却一点也听不进去,非要把父亲送回老家种地不可。说心里话,当时的父亲倒并不怎么害怕高老板开除他,也不害怕族大爷骂他,训他,罚他不让他吃饭。父亲或许还负气地认为,东源盛开除了我有什么,只要我人在济南,将来,说不定哪一天,济南还有西源盛,北源盛,南源盛等着我呢。此地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啊。至于族大爷的骂,训,罚他饿肚子,那也应该,谁让你无端耽误了送货,给人家掌柜的惹了事端呢?但是,父亲最害怕的,就是叫他再重新回到那个贫穷的农村老家去,当一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父亲最清楚不过了,当年的爷爷,在沂水县登楼店一个当铺干工,爷爷每年虽然也能添补家中几十吊钱,但是这点钱对于一个五口之家,不过是杯水车薪。家中的生活非常困难,奶奶一年到头给人家帮忙做饭,每晚回到家,带回几个主家送的小米煎饼,大伯和父亲,小姑每人分一个,喝碗棒子面稀糊粥,就算吃了晚饭。由于不堪忍饥挨饿的日子,大伯14岁就外出学徒去了。父亲到了上学的年龄,因无钱交学费,也只好跟二大爷上学读书,也是半天上学,半天回家干活,除了上坡拾柴草外,还得推磨推碾。有时早上跟爷爷赶集市拉小车,去卖地瓜,下午再上学补课。正是这样的苦日子给了父亲很大的教训,使父亲从小懂得了只有长志气,脱离这个贫苦的农村,才能有好日子过。
父亲只有哭求不走。父亲跪在地上,给族大爷连连磕头,认错,说看在老家爷爷的面子上,饶了他这一回,今后,他保证再也不去参加学生游行了!
父亲虽然表面上对族大爷苦苦哀求,郑重表示,承认错误,但心里面却暗暗骂族大爷是汉奸,走狗,父亲骂族大爷不是中国人,要不怎么会不支持学生呢?日本鬼子多可恶呀?父亲甚至还暗下了决心,等哪天我要是有了枪,第一个先崩了族大爷!
后来,族大爷见父亲确实害怕了,才软了心。就答应暂时叫父亲在他所任职的济南院东大街恒庆昌银号闲住着。也是事有巧遇。隔几天,族大爷的母亲来济南看病了,身边一时缺少侍奉的人,即叫父亲去帮忙去了。父亲在四舅母身边,每天除了上街买菜,即在家帮着做饭打杂。这样虽然暂能栖身了,但是对于一个向往外边世界的男孩子来说,思想上也是很痛苦的。所以,有时候,乘四舅母不注意,父亲利用外出购物的机会,还是憋不住又偷偷跑到静坐的学生堆里,东串西溜。
许多年以后,有一天,当年届八旬的父亲,又在他那应与其同居一室的我这个三儿子之请求撰写的个人回忆录里,写到了发生在一九一九年春天的那场学生潮时,竟然无意间向我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当年年仅15岁的父亲,自打那天看见游行队伍前边喊口号的那个束长发的漂亮女生后,印象特别深刻。父亲那几天之所以一直坚持送饭,爱国心是一方面,更多的,却是父亲心里面一直渴望能够再看见那个漂亮的高挑身材的女大学生。然而,叫父亲失望的是,那几天,他在学生堆里转遍了,却始终也没有再找到那个漂亮的女生。还为此耽误了大事,险些被撵回老家,重新务农。
这样闲散无聊地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其间幸有四舅母帮父亲说情,族大爷最后才又答应,把父亲又荐到西关西杆面巷恒庆公银号去学徒。
而这时候,学生们已经闹了几个月,后来听说国联已经答应了我国人民的要求,叫日寇把胶济铁路交还中国。这才结束了这场运动,学生上了课,商店开了市。
虚惊一场
一九四二夏天,三十八岁的父亲,正值官运亨通,事业辉煌的鼎盛时期。用他在自己那本颇具传奇的个人回忆录里面的话说,这段时间,是他 一生中的黄金时期 。
这天过午大约三点多钟的时候,父亲正在济南北洋大剧院楼上包间里听程派名戏《锁麟囊》,正听到兴头上,湘灵隔帘让丫环以锁麟囊慷慨相赠也在同日出嫁的贫女赵氏,忽然,意兴阑珊、翘腿吟唱的父亲看到店里的小伙计顺子,气喘吁吁地跑上了楼。顺子一路跑到包间,跑到父亲身边,神色慌张地凑到父亲耳朵上,低声嘀咕了几句什么。父亲的脸色,立即就灰了下来。
父亲没再说话,而是匆忙起身,跟身旁陪着自己一道看戏的刘耀庭告辞。
刘耀庭是济南西关花店街福顺永布店经理,父亲的知己朋友。这几年,刘耀庭一直供应着父亲济南宏章制服厂的原料棉布,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拥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布店老板,刘耀庭还经常带领父亲去棉纱关,进行棉纱棉布的交易,并用他福顺永的名义给父亲招揽生意。因此使父亲获得不少利润。有时候遇到父亲手头一时紧,没有现钱,只要去一个,他老兄就会慷慨大方地赊给父亲,布料、棉纱那是倾尽所有地尽量供给父亲使用。刘耀庭这个老朋友好喝酒,父亲和他也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这不,今天一大早,父亲就是刚从南门里裕泰银号取了钱,叫上刘耀庭,在聚丰德吃完饭,一块来北洋看他们最喜欢看的程派名戏《锁麟囊》的。
刘耀庭看父亲脸色不对,一把拉住父亲: 守珠,遇到什么事了?别紧张,说给你哥我听。
原来,就在半个小时以前,有两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大鼻子外国人,忽然闯进了父亲的宏章厂。他们一下汽车,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店里,不等落坐,就咿哩哇啦乱说一气。中国翻译对店里的人说,你们经理呢?我们要找他谈谈。店铺员工看这几个人来头不小,都有些胆怵。关键时刻,母亲周旭东挺身而出。周旭东看情况不妙,就对翻译谎称,经理已经出外地了。先生你们是哪里的?周旭东对翻译说,有什么事跟我谈好不好?我是他夫人。翻译立即对两个外国大鼻子如实汇报了,那两个外国大鼻子满腹狐疑地上下打量了母亲一遍,将信将疑地摇了摇头。
我们有事找他,你必须把他找来。让他和我们见见面,有事谈。两个外国大鼻子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那这些人现在在哪里? 刘耀庭的神情也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后来这伙人看问不出什么结果,临走留下了他们的现住址,纬一路信华旅社10号房间。就扬长而去了。 小顺子赶忙替父亲回答。
傍晚,刘耀庭过来看父亲。下午从戏园子出来,父亲就搭洋车去了纬四路的东华旅社。东华旅社经理吕文斗是父亲的老朋友,平日父亲也常去东华玩。吕经理得知了父亲白天遇到的这件蹊跷事,也感到凶多吉少。吕经理当即挽留住父亲。为了父亲的人身安全,从此以后,父亲就决定暂时住在东华,不再露面。先躲几天,看看风头再说。
刘耀庭和吕文斗看父亲惊魄未定的样子,都摇头叹气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耀庭、文斗,你们都帮我分析分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父亲放下水烟袋,紧张地叹了一口气。
刘、吕二人面面相觑,哑口无言。还说什么呢?一晚上了,两人安慰了父亲不知道多少遍了,也帮父亲分析来分析去,根本就分析不出什么结果。大家都说:父亲在济南做买卖诚信守法,一辈子没得罪过任何生意场上的人;到金菊巷找 ,也从未赅过老鸨的账,情场上也不会有什么仇人;至于工厂里对工人,父亲更是谈不上苛刻吝啬,无论是低谷时织袜子捲土烟,还是辉煌时做制服大老板,父亲都是照章办事,按时发饷,从没欠过一个徒工的一个铜板。谁不知道呢,现在的父亲是济南工商界有名的 秦二爷 ,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父亲从来就是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
让大家更为纳闷的是,洋人在父亲的生命中一直是一个空白,到现在为止,父亲还从未跟洋人打过任何交道呢。那么,这些来历不明,身份不明的洋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这样火烧火燎地跑来找父亲,这样急于要见到父亲,又究竟想干什么呢?
从这天起,父亲就再也不敢回家了。在那段日子里,父亲是今天在这儿住一天,明天又到那儿住一天,像耗子躲猫一样,战战惊惊,四处躲藏。当然了,父亲的所到之处,也都是住在他的那些熟人朋友的地方。
这样躲在外边大约有七八天左右的时间,一日,父亲的好朋友游恩勃来宏章找父亲。了解到店内介绍的这些情况后,游恩勃二话没说,起身就去了信华。
游恩勃在济南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过外语,会说英语,日语,加之这人本身就在政府部门上班,官场上的人,见过世面,又好打抱不平。帮助朋友,也就是在所不辞的义举了。
游恩勃见到这些人,开门见山:
李理事长是我的朋友,他现在出门在外地还没回来。你们有什么事直接对我说吧。
两个外国人看到游恩勃一副处事泰然的镇静模样,有些气不打一处来。
我们找的是李理事长,找你有什么用处?你是干什么的?
游恩勃坦然一笑,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又对两个外国人说: 李理事长已经全权委托于我了,由我跟你们交涉。
这几个人见来者不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本身又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便收敛了许多。尤其是游恩勃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对话,更让两个洋人刮目相看。
洋人说: 树子是李理事长的亲戚,他私通八路,是我们把他从北京保释出来的。按照行间规矩,作为树子的长辈,李理事长必须支付一笔保释金给我们。
游恩勃听得一头雾水,便不敢冒然多言。从信华出来,游恩勃又匆匆找到父亲,寻问此事。
父亲思忖了半天,忽然一拍脑袋: 噢,我想起来了!
原来,父亲的族孙中确是有个乳名叫树子(大名李景树)的。他在院西大街萃华银楼干店员。去年萃华银楼给巨野做了一批银质徽章,还没出手,就让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认为这是给解放区八路军制做的。半年前的一天,日本人忽然到萃华捉人,竟把树子抓到日寇的宪兵队去了。后来不知怎的,日本人又把树子稀里糊涂弄到北京去了。从那,济南就再也听不到树子的任何消息了。树子到了北京后的具体情况究竟怎么样了,父亲这边也就不得而知了。
父亲忽然说: 是不是这几个人已经把树子押回济南了,他们想借机敲我的竹杠啊?
游恩勃当即肯定地说: 嗯,很有这个可能。
受父亲之托,游恩勃当晚便去了一趟萃华银楼。萃华的马老板介绍说,树子现在人确实是回来了,但是他目前并不在店里,树子现在还在宪兵队扣着呢。
马老板回忆说,前天他去要树子,树子哭哭涕涕对他说,他对不起族爷爷(即我父亲)。树子回忆起那天他们在由北京回济南的火车上闲谈时,是他无意中把族爷爷的名字告诉了这两个波兰人。树子说俺族爷爷现在发财了,不但坐上了市军服公会第一把交椅,手下还掌管着好几十个工厂呢。可能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伙押送树子回济南的宪兵腿子,顿时起了歹心。不错,果然他们几个是想借机敲诈骗财的!
两天后,游恩勃又一次来到了信华旅社。这一次,游恩勃代表父亲郑重向对方提出三点声明:第一,树子与李理事长虽有族亲关系,但这对树子的所作所为,对树子的人质释放,并不构成任何连带和承担所谓保释费用的任何理由与义务,因为树子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李理事长作为商会的负责人,不需要承担对萃华这个所谓祖孙的监护权的任何义务和权利;第二,李理事长身为民间组织负责人,他平日只负责商会的沟通管理,不掌管财务;第三,李理事长现在人在南洋养病,年内不会回国内来的。
洋人说: 你说李没有钱,我们不相信。作为军服工会理事长,他手下管着50余家商店服装店,连日本人都败在了他手下呢?
游恩勃心里笑骂道,这些洋鬼子!信息还怪他妈灵通呢,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呀?嘴上却说: 你们弄错了,财务大权掌握在会长手里!
关于两个洋人所谓 连日本人都败在了他手下 的事情是这样的:原来,父亲从1940年被业内商家推举为济南军服业公会理事长以后,按照投标的办法,多次与山东省伪保安总队交涉。因为在这之前,省内所管辖的保安队统统都由总队包揽订做服装,由省伪保安总队的日本顾问找日商承做。我们中国人的服装店都得不到承做。但是由于日本商人承包的价格太高,父亲按照商会的安排,积极把我们公会下属业户组织起来,准备与日商的布帛组合(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纺织行业组织)展开竞争。日商闻讯后顿时惊慌不安,他们料到自己会在竞标中失败,便主动来找我们的公会谈判。谈判桌上,父亲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同时又很注意掌握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就这样,经过十几轮艰苦的协商后,双方最终一致同意,从这年的秋天开始,凡是保安队的服装,均由日中两家分做 从此,在济南军服界,终于结束了山东省伪保安总队统一订做服装由日商独家承揽的历史。
洋人不甘失败,又眨眨眼皮说: 我们听树子说,理事长是个朋友人,我们是想跟李交个朋友的。
游恩勃哈哈大笑说: 你们想交朋友,那也要等理事长回国以后再说!
洋人彻底没辙了,最后只得尴尬地搓着双手,嘻皮笑脸地作乞讨状: 你看,我们在这里等了他一个多礼拜了。你给理事长说说,叫他拨点差旅费打发我们回去总可以吧?
此时游恩勃见大局已定,估计阴沟里翻不了船了,便蔑视地瞅了两个洋人一眼,冷笑一声: 哼,我们理事长不是慈善家。告辞了!
几天后,游恩勃从有关部门的熟人那里了解到,这几个人(包括那两个大鼻子波兰人)果然都是些日寇的宪兵腿子,这次他们确是打算借树子敲诈父亲一笔钱财的,幸亏是朋友帮忙,虚惊一场,父亲才免了这次的敲诈。这次恐怖事件结束后,父亲便携重礼,亲自登门致谢游恩勃。并于三日后,在燕喜堂摆下盛宴,盛情款待在这次恐怖事件中所有关心、帮助过自己的朋友们。
救火
一九四八年农历八月初八,离解放军攻打济南城还有七八天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济南城内,时局混乱,局势失控,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老百姓苦不堪言,人心惶惶。
这天早上,父亲的旅馆里突然闯进来20多个穿军装的国民党士兵。他们荷枪实弹,杀气腾腾,从大明湖南岸的省图书馆匆匆跑到位于湖畔附近后宰门街15 号的济南明湖旅馆。这伙人一进旅馆,立即就用粉笔在大门写上 国民党第四兵监分队 字样,并派兵站上了岗。当时父亲弄不清这帮人中谁是官,谁是兵,眼巴巴看着他们强占了六七个房间,把原来入住的旅客都撵走了。店里的也不准任何人使用,由这帮国民党兵把持着。
战事越来越紧急,解放军兵临城下。市内开始落炮弹了。
怕死的国民党士兵听见炸弹响,都吓得纷纷往防空洞里钻,把旅客和父亲的家属都从防空洞里撵了出来。父亲旅馆里唯一的一个防空洞就这样叫这伙土匪式的士兵独自强占了。为了躲避炸弹危险,父亲在他住的后院北屋东山墙下架起两个紫檀条几,上面棚上20多床绸缎棉被,父亲和母亲躲在条几下避难;在北屋西间山墙又架上两张八仙桌,也棚上20多床绸缎棉被,我姐姐和我哥哥在里边避难。父亲几次叫当时病重的我奶奶和我大娘过来,无奈两个乡下女人都怕闹心,大胆地呆在南屋死活不肯出来。父亲眼看劝阻无效,最后只好作罢,是死是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天夜里,战事更激烈了。济南城里的大街小巷,炸弹一颗接着一颗地落下来,又炸响。父亲知道,解放军大部队快要攻城了。这时候,在父亲旅馆前院二号房间的后墙外,一颗炮弹突然炸响,硫磺弹点燃着东邻申家的西屋,大火迅速着起来了。
救火啊!
七八个国民党士兵发现了大火,急忙从防空洞里跑了出来。他们把旅客逐个都叫出来去救火。因为火大,直向旅馆二号房间这边扑来,情况十分危急。旅客和国民党士兵一人一个洗脸盆,20多个人列队从河道上楼梯到三号房间的窗前(三号房间是楼房),一盆水一盆水地传递。但是,这时候必须有一个人越过窗外,站在二号房间房顶,才能把水泼到东邻的烈火上。危机关头,找谁,谁也不敢去干这玩命的活计。
这时候,就见一个络腮胡子的国民党,忽然跳出来,大声叫喊: 叫掌柜的来!
立即就有两个国民党士兵端着枪,越过墙,跑到后院父亲的房间。 滚起来,快去救火! 当时,四十四岁的父亲正患病在身,发高烧,不能动。母亲赶紧爬出条几,给两个国民党兵跪在地上,哭求他们放过父亲,掌柜的正发着烧,不能去。这俩士兵哪管你生病不生病,不等母亲说完,一脚踹翻母亲,从条几底下拉起浑身颤抖哆嗦的父亲,就往外走。国民党士兵把父亲拉到楼上,从窗户里一把将父亲推出窗外。父亲一时站立不稳,险些从屋顶摔下跟头。父亲只好战战兢兢地骑在屋顶上。
窗内一盆接一盆地将水递给了父亲,他们叫父亲赶紧往火上泼。但是,当时父亲高烧40度,烧得人头重脚轻、四肢乏力,哪里还有力气泼水救火?两个国民党士兵在窗内骂不绝口,口口声声威胁父亲说,再不好好往火上泼去,老子就他妈枪毙了你!父亲当然知道,这时候,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们要杀一个人,是很随便的,举枪就杀。当时的情况非常可怕。父亲骑在屋顶上,两耳旁呼呼生风,看见济南城漆黑的夜空,犹如乱窜着成百上千条火龙,这些由炮弹燃成的火龙东奔西突,纵横驰骋,织成了一片火海,炮声震耳欲聋,满天都是火光。
正在这危急时刻,父亲忽然听到 轰隆! 一声巨响,刹那间,就看到灰土满院、砖瓦乱飞,屋下这伙救火的人,也早吓得惊叫着作鸟兽散。父亲赶紧趴在房顶上,但是他这时候全身上下都开始冒火了。原来,是屋顶上的硫磺弹液沾满了父亲身上的衣服,等他清醒过来,才看清屋下那些救火的家伙们,早已经吓得一个个不见了踪影,不知道都躲藏到哪里去了。父亲便赶紧从窗外爬进屋内,顺着楼梯,河道,好不容易爬到了后院的房内。这时候,躲在屋内的母亲,看到父亲像一个火人似的浑身冒着火爬进了屋,顿时吓得惊叫一声,赶紧上前把父亲的衣服统统扒掉,然后再把那些正在燃烧着的衣服放到一个大盆里,倒上水。这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吃惊地看到,那些泡在水盆里面的衣服还一直哧哧冒着火光呢!
原来,刚才在四号房间上落下一颗炮弹,炸掉了半间房顶。因为有三号这个楼房的墙挡着,父亲才没被炸伤。这颗炸弹的爆炸,把父亲从九死一生的险境中救了出来。然而,就在父亲和母亲刚又钻进条几下避难的时候,忽然, 轰隆! 一声,外边又是一颗炮弹落到父亲屋的东间,瞬间就炸去了半间屋顶,把床上的麻纱帐子炸出了十多个大窟窿,床上的缎子被子也被炸了五六个大洞,从屋顶塌下来的土石瓦块,瞬间就把条几下父亲和母亲的下身都埋了个结结实实。就在这颗炸弹爆炸的同时,西间屋顶也落了一颗炮弹,炸去了半截山墙,幸好房顶没落下来,否则,我姐姐和我哥哥两人就难免遭危险了。然而,更为危险的是,这时候,在父亲头顶的窗正外边,也落下一个没有爆炸的大炸弹,如果这颗炸弹爆炸了的话,那么,我父亲就肯定地不能幸免这一次的危险了;而如果我父亲一旦真的被这颗炸弹夺走了生命的话,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也就肯定不会有我这个排行老三的儿子的存在了,因为,济南解放以前,我还没有出生呢。
直到济南解放半个月以后,母亲才发现这颗炸弹。炸弹钻入地内有一尺余深,地表仅露着炸弹的后半部分,因为炸弹的后半部分有三个铁翅子,所以炸弹钻入地面时被地皮挂住了。母亲看见后不认识是什么东西,叫来别人一看,才说是炸弹。这时候,全店上下顿时又都惊慌起来。
父亲马上跑到公安部门去报告,一会儿来了武工队,才把炸弹起出来,足有三尺长的一个大炸弹。等武工队的人弄走了炸弹,大家这才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都说真危险啊!如果这颗炸弹爆炸了,父亲住的整个三间北屋,必将被夷为平地。
一九四八年农历八月十五,天刚亮,解放军大部队就攻打进城里来了。龟缩在父亲旅馆里面的国民党士兵,这时候都开始惊慌失措地四处寻找便服,他们把自己身上的军服统统扔掉,换上从旅客身上强行扒下来的衣服。那个满脸胡渣子的兵痞,不但抢去了父亲的便服,帽子,连母亲的单裤、夹裤也都掠走了。他们匆匆忙忙换上各种便服,企图充当老百姓,乘混乱遛出城外逃走。解放军冲进旅馆后,把所有没来得及逃跑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不剩地都带走了,枪支弹药也都全部没收。那些抢了父亲和亲眷们便服冒充居民的士兵,听说逃跑到济南北关城门时,被把守关卡的解放军查出来,也都被带走了。其中就包括那个络腮胡子,经查这家伙竟然还是国民党第四兵监分队的一个副队长。
广州换锁电话荆门治白癜风专科医院益母颗粒与益母草丸- 12-29[武侠]布里奇斯季后赛单场据估计30分&4三分&4帽 历史第7人&比肩詹杜科
- 11-14[武侠]Alessandra Rich 2022早秋系列,修身廓形的韵味,亮点更添时髦
- 11-11[武侠]率先8个风华音乐大师工作室落户宁波大学
- 10-27[武侠]地球磁场缓慢移动,磁场强度下降10%,地球或将已是下一颗火星?
- 10-22[武侠]投资者提问:二季度制造任务紧张吗?有什么技术上的新突破吗?
- 10-17[武侠]曾年销30亿的“神酒”江小白,为何如今无人问津?假象原因太现实
- 10-03[武侠]近一个月股价跌近50%,傲农生物:4月份起生猪出货头均毛利较一季度已明显改善
- 10-02[武侠]新纪元古玩艺术品在线模拟器:精品推荐——佳品磁铁陨石
- 09-30[武侠]西安旅游职业中专研议陕西省高水平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名
- 09-28[武侠]又挖多特?哈兰德3月曾接触拜仁 双方拜访一个小时
- 09-07[武侠]长春视觉艺术生文化课英语学习方法,高三学校分享
- 08-27[武侠]微软大受欢迎《壮志凌云 2:独行侠》联名款 Xbox Series S 主机
- 08-10[武侠]蔬菜中蕴含的中医知性:芹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