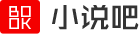前世江南二
你可以想象,这是在白居易或者韦应物的姑苏城内。
姑苏城是狭义的,但我更习惯于叫它江南。广义的江南摇摇荡荡,古典的夜色中弥漫着丰富的现代气息。伫立于渡僧桥头,我看见游船带着灯火来来往往,把斑斓的山塘河水推向了一天中最兴奋的时段。
民间的巷子里,月光不转朱阁,不抵绮户,却一样可以照你的无眠。
你信不信?我曾见过晚唐的山塘街,桥拱朔月,灯影斑斓,云水荡出新欢;我见过南宋的山塘街,夜色消瘦,丝竹委婉,相思远了客船;我还见过明清时期的山塘街,荷笠戴斜阳,评弹与小唱,公子王孙的富贵地,文人墨客的风流场…我活过那些岁月,在姑苏城里城外,我渔樵耕读过,琴棋书画过,诗酒花茶过—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那窗口洞开的三层阁楼上,曾有红酥手为我铺纸研墨,为我红袖添香,我或许还在此画过不少春宫图,写过不少禁毁小说呢。繁华拥挤的巷子里市声温软,或许每一位白面书生都曾擦着我的右肩匆匆而过,形同陌路;或许整条街上的女子,都曾经枕过我的左臂,随我翻滚,随我辗转呢。
你信不信,我的前世必定是风流的,精彩的。我那么懂得爱,却又是那么喜欢哼《长恨歌》我那么不近兵戈,却又是那么爱吟《从军行》我的娘子其实就是被我移花接木的诗歌和半清半浊的男中音一步步勾引成妻妾、成母亲乃至成为祖母的。在粉墙黛瓦的水景房内,直到有一天,我看着她慢慢地老成了一缕炊烟。老成了一缕炊烟还那么韵致。
而今,我走在七里山塘,一切都耳熟能详,桥还是那桥,有平仄,有起伏,也有弧度;巷子还是那巷子,有贫富,有是非,也有曲直。除了年代,一切都没有很明显的破损。只是,走着走着,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走不见了,我的爱跟着我一起走不见了。我们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悄然走失,与此同时,仿佛又在凌乱的错觉中,完成了几个世纪的转换与轮回。
不知不觉,阊门近了。卧波的长桥已改头换面,不再依赖于青石条结构,而是和钢筋水泥抱在一起,伸向民国风情街,收集和风细雨,承接阳光月色。而每当夜幕低垂,这一带的灯火已是空前的,大运河与山塘河披着彩衣在此交汇,聚散无痕。
我敢肯定,我的娘子是不会轻易在阊门附近出现的,除非繁华散尽,流萤从花草中结队飞出。除非晚风轻如薄翼,有勾魂的琵琶声自远处细细地飘来。然而,当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时,我只能边走边看,在街灯下不断重复眺望远方的动作。如果此时有人问我:你来自哪里?那我就会如实地告诉他:我来自故国。是的,我来自故国—那里,山河曾经破碎,但已经被缝好,不是用蚕丝,而是用爱恨。爱是必须的,因为天地,因为人间;恨也是必须的,因为战火,因为残缺。爱与恨就像一件精美的苏绣,它的正面和反面,必定有着截然不同的针脚。
有位江南女诗人曾经说过淡仇者必定寡恩—我深深地认同。此刻,我的爱人要是知道我在想什么该有多好啊!如果是这样,即使这个世界再无趣,我们也会很有趣。如果是这样,我们夹在唐诗中的旅程,将不会再有七言的烦恼和五言的哀伤。何况出了阊门还是姑苏,出了姑苏还是吴越。
这才是我一直想要的旅程:古风不逝,良缘未竟,却换了人间。换了人间,却良缘未竟,古风不逝。一切都在光阴和梦中循环。
此刻,我很想对着夜空大声呼喊,很想放肆地跺跺脚,听桥孔和青石板同时发出亲切的回响。我其实是想再次确认:在江南,凡是能被我唤醒的,都是与我有关的。
你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