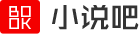格非喧嚣时代的隐语者
朋友们都说,格非忽然要红了,到处都看到他的消息。但格非一直是这种状态,他的文学作品有一种长久的魅力,总有一部分忠实的读者,对他的作品迷恋。但格非不是流行作家,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都跟流行,跟时代的趣味,有着鲜明的自我立场。格非的写作,一直保持着特殊的文字气息,他虽然从历史叙事进入现实幻境,但文字的风格,并没有太大变化。 我总觉得,要写格非,先要回到过去。回到过去,就得进入青年记忆。 翻墙的格非 我可以从一片梧桐叶写起,从草坪谈天开始,亦可以翻墙去喝酒开头。念书时,我们在格非的带领下翻越华东师范大学枣阳路后门,成为某种特殊的记忆。然后我们自己翻墙,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我认为,理想的大学校园,学生应跟老师住在同一个小区。在校园里散步时,学生能看到大教授的身影。课堂之余,可以去年轻教师家串门,喝酒,聊天,争论。一名大学老师要带学生一起翻墙 翻越有形之墙和无形之墙。我的大学记忆,就在翻墙和上树中度过,其中有格非的各种身影。 前些天美国著名电影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去世,激起我们很多怀念。他在《死亡诗社》里扮演的教师,成为很多大学青年教师的模仿对象。我上大学第一课,碰到一名 到了有些神经质的老师。上课前,他在文史楼三楼教室讲台区来回踱步,一会儿看天花板,一会儿看窗外,一会儿自我冥思,就是不正眼瞧我们一下,让我们这些前中学生觉得哪里犯错误了,感觉惴惴不安。他手捏大前门香烟,鼻冒火车头白烟,对我们一脸不屑。仿佛面对我们这些脑子里被洗得刷白的前中学生,他心里充满了怜悯、甚至憎恨。 上课铃响,他走上讲台,我内心涌现出一句洪亮的声音:“上课!起立!” 前中学生们早就被训练得如同马戏团狗熊,产生巴甫洛夫反应了。 班长腾地站起来,口令还没有喊出来,他轻轻摆手,如武林高手隔空点穴,可怜班长就被点得瘫软摇晃,口令在口腔里打转,憋得满脸通红。 “不用起立,不用喊老师好,不用坐直,不必用心听。”老师还是看着天花板,说话很轻,如山西师傅刀削面,“你们随便听,也可以干别的事情。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可以回去睡觉。” 他的话如鞭子般撩在我记忆深处,“这本教材是垃圾,可以直接扔掉……” 这不是格非,是另外一名特立独行的老师。格非相反,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和他的叙事风格一样温和平顺,不会如此极端。他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会温和地说出,甚至不说。很难想象,格非如何在年轻时就能形成独特的文字风格。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文字一望便知,格非的文字,打着他自己深刻的烙印,混在任何的作家中,都能一眼就看出来。但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形成这种文字风格的。 追问“过去”的格非 格非早期以先锋小说知名,他对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有精妙的描述,如短篇小说《青黄》里对“九姓渔户”的推测和演绎,最后归于初始的疑问,并消解无形。让我们觉得,所有那些繁复的猜测、考证,都是无意义的。中篇小说《迷舟》从北伐战争中的一个小小的疑点开始,发现历史可能是被一个错误而推动的。旅长萧回到家乡,被可笑的错误抓住,最后却遭到了警卫员的判决。这些在历史书里不会呈现,历史书只是描述了一场失败,但不告诉我们细节。因此,先锋小说家在历史的细节中,找到了中国现当代整体历史的破绽,而让我们对历史的抒写产生了深刻的疑问。在那个时候,小说在文化反思中,走在了前列,并推进入到历史脉管深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有一个被批评家称为“新历史小说”的派别,代表作家作品如莫言《红高粱》等,都在那些此前似乎已经被历史书写得毫无疑问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找到了故事推进的空间。 格非当时是年轻的先锋小说家,他与余华、苏童、北村等同行一起,有意避开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而进入了对历史书写的疑问中。通常,一个特殊人物的存在,让我们所认识的历史教科书历史变得荒唐可笑。例如余华的《活着》里,那位怪异身份的福贵,就破坏了我们对泾渭分明的革命者与反动派的认识,而显示出了历史的诡秘之魅力。 专注“不牢靠”的格非 作为一名南方作家,格非在苏南的历史流风中,浸润了特殊的叙事品格。他那时的作品时间通常不发生在现实,而是在过去。同时,你阅读那些小说会发现,所谓的过去,也是可疑的。我们不应该立即相信被某种历史观念梳理过的过去,而是要重新开始思考历史与现实。历史一旦可疑,那么,现实也不可靠。同时,即便是表现现实生活情态,格非笔下的人物关系也是不可靠的,例如他的早期重要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在大学的背景下,凸显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陌生感。一个叫做张末的女生,让道貌岸然的大学教师显露出了“欲望”的原型,而这一切,在此之前都是被掩盖的。格非对人与人之间的表面关系,有一种深刻的怀疑,如同他在早期小说里怀疑主流历史叙事那些貌似确凿的事件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格非在“江南三部曲”最后一部《春尽江南》里,塑造了一名没落诗人谭端午与社会现实的不协调感,他跟自己的妻子完全不协调,甚至跟自己也完全不协调。他是那种试图泯然于众,但处处无法融入的人。在自我的世界里,谭端午找到一种特殊的慰藉。这个自我世界,建立在他对音乐的迷恋中。一旦音乐响起,前诗人谭端午就从现实中消失了,他对音乐器材的迷恋,远超过他对妻子的感情。从小说的角度来看,谭端午本来应该是一名道德高尚的正面人物,这样他更能以悲情对抗一个荒谬的世界。但谭端午自己的道德并不牢靠,他曾在欺骗一名女粉丝之后,把女粉丝裤兜里的钱都掏走。 同时,大时代背景的失踪,让谭端午无法找到类似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塑造的托马斯那种反抗体制的悲情英雄背景。托马斯是不妥协于体制而被体制排斥的,他在做玻璃清洁工时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深刻同情,他对特丽莎的复杂情感,他忍不住地跟各种女性发生关系的人生混乱,都不能阻止他在小说中走向圣徒行列 虽然米兰·昆德拉很谨慎地给予托马斯一种偶然的解脱:车祸。但谭端午却缺乏这种悲情的背景,他的问题都是现实的:他鄙视世俗,却无法逃离世俗,甚至依靠世俗的力量,来营造自己的脆壳空间。 格非很敏锐地发现,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常态,很多人以此为乐。谭端午和他妻子之间,本来有一个诗意的联系,但妻子变成有成就的律师之后,他们的关系异化了。 在格非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隐身衣》里,格非把在《春尽江南》里无法发挥出来的对音乐、对音乐器材的独特知识,淋漓尽致地加以表达。在北京,手工做胆机的人不超过二十个,而且他们都老死不相往来。而我们的主人公,却在得到聘用给一名土豪做胆机的时候,发现土豪莫名其妙地死了,并且卷入了另外一件更加莫名其妙的婚姻中。而他对自己的妻子,一直很陌生,这位被毁容的妻子,似乎穿着某件隐身衣。 就像我们不能真正知道历史,我们也不能真正知道彼此。现实与历史,在这里,完全混淆了。格非的叙事具有某种特殊的趣味。同样的现实,并非铁板一块的,我们在现实中,并不一定认识现实,人与人之间,有着深刻的隔阂。 奇怪的是,在格非的小说里,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感超越了亲和性。或许,这也是后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特殊景观。 作家面对现实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转身离开,一种是进入多重现实中,让这些所谓的现实暴露荒谬的本性。 (:王谦)
怀孕左腿疼是怎么回事
孕期缺钙喝什么汤好
孕妇小腿抽筋怎么按摩
小便发黄好治疗吗控制体重才能控制人生
儿童补钙什么牌子好
- 12-29[武侠]布里奇斯季后赛单场据估计30分&4三分&4帽 历史第7人&比肩詹杜科
- 11-14[武侠]Alessandra Rich 2022早秋系列,修身廓形的韵味,亮点更添时髦
- 11-11[武侠]率先8个风华音乐大师工作室落户宁波大学
- 10-27[武侠]地球磁场缓慢移动,磁场强度下降10%,地球或将已是下一颗火星?
- 10-22[武侠]投资者提问:二季度制造任务紧张吗?有什么技术上的新突破吗?
- 10-17[武侠]曾年销30亿的“神酒”江小白,为何如今无人问津?假象原因太现实
- 10-03[武侠]近一个月股价跌近50%,傲农生物:4月份起生猪出货头均毛利较一季度已明显改善
- 10-02[武侠]新纪元古玩艺术品在线模拟器:精品推荐——佳品磁铁陨石
- 09-30[武侠]西安旅游职业中专研议陕西省高水平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名
- 09-28[武侠]又挖多特?哈兰德3月曾接触拜仁 双方拜访一个小时
- 09-07[武侠]长春视觉艺术生文化课英语学习方法,高三学校分享
- 08-27[武侠]微软大受欢迎《壮志凌云 2:独行侠》联名款 Xbox Series S 主机
- 08-10[武侠]蔬菜中蕴含的中医知性:芹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