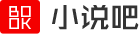当代作家评论刊发郑小驴论http
郑小驴论
兼及一种 青春文学 的再生
金理
一 同时代
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对象,青年作家郑小驴,是我的同时代人, 出生于同一时期、具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因而显示出相类似的精神结构和行为式样的同时代人 (引自陈映芳《世代论与青年研究》,《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第 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在社会学家看来,当我们试图理解社会和精神运动的结构等问题时, 代际 或者 世代 的考察视角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向导(参见卡尔 曼海姆对 代问题 的研究,收入《卡尔 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因了共同承受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同时代人会形成此一代际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结构乃至群体意识;但无疑,即便共同于一段时空而存在于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也不可避免形形 的差异。诚如彼得 伯克提醒, 世代 应该被处理成 想象的共同体 , 每一代的成员分享某种经历和记忆, 他们可能没有共同的信仰或价值观,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相同的境遇 (引自彼得 伯克(Peter Burke)《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182页,姚朋等译、刘北成修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所谓的 同在 、 同时代 ,并非假设同质、合流、无差别,而是预期在众数、多元、异质、个体、对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参与、 不齐而齐 。且如董启章所言,正因为知觉到差异甚至是鸿沟的存在,故而 必须为理解或沟通搭建一条可行的桥梁。这样的桥梁一旦建成并且被踏上,大家就有了成为广义的 同代人 和 同世界者 的基础 (引自董启章《答同代人》 序 ,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19 年,鲁迅在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期写过一首诗: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以此表达当年的战友 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 之后 布不成阵 的寂寥,显然在鲁迅的追忆中, 五四 的辉煌、文学与文化喷薄的创造力,离不开那代知识分子的通力合作,同时代人在精神的旗帜下集结,建成了一座元气淋漓的 桥梁 。同样,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在于杰出作家和批评家的比肩而立。文学尽管是 个人的事业 ,但同样需要同时代人的嘤鸣激荡之声,相互应答、分享、承担和创造。
同时代 不仅意谓着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也指向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 , 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 但正是因为这种境况,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 (吉奥乔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既 附着 、内在于时代,又不是泯然陷落在时代中;有能力保持对时代黑暗的凝视,还要有能力感知黑暗中的光。下文讨论郑小驴的 鬼魅叙事 时,我将再次照应这一意义上的 同时代性 。
写作终究是件漫长的事情,就好比马拉松赛跑, 80后 这一代里,是曾有过一批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想文学并不是百米冲刺,拼的是耐力和能否熬得住一万米过程中的寂寞。我想我还在路上,并将永远在路上,而文学,本就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事。 小驴的这段创作谈有很多层意思。在今天中国的写作现场(包括阅读与出版现场),分野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跑得很快 的那批人早已暴得大名,而一天码上万字的作者们也有丰厚的市场利润回报,然而小驴并不焦虑,他目光坚定,脚步不游移,他有自己的选择,心有所钟,信之弥坚。此外,我和小驴是 同时代人 ,因为感知结构、知识趣味、文化修养的近似而容易引发艺术审美的共鸣 不过,我还是想从小驴的话里再引申出一层意思:当我在追踪阅读小驴的创作、进而展开评论时,我同样面对着 一眼望不到尽头 的局限性视野。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 同时代性 ,意味着一种身处局限性中、特殊的研究姿态和方法。打个比方,文学如同不绝长流,设若我们要了解同时代的某种文学潮流的演进情况,一种工作方式是,将自己化作置身于此一河段中的石头,感同身受水流的实感;另一种工作方式是(如果我们个体的生命长于这一段文学潮流),站在岸边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或捡拾退潮后留下的时代 遗物 ,带回实验室作研究。在以上两种姿态中,后者往往因为确定了潮流 结局 的绝对性以及将认识对象固定化,而得出结论予人 正确 、 客观 的印象,同时 置身事外 提供了优越感,于是负起 指导读者、批评作者 的大任;前者丧失了后见之明的支撑,其判断很可能与文学史后来给出的 结局 不一致, 在同时代史的认识中,不可避免地要包括预测的成分。 把对象置于总体当中,在流动性当中加以把握 (孙歌:《文学的位置》第166页、16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这是孙歌对日本历史学家远山茂树研究方式的评述。我参引过来表达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下一节那段 作为生活在历史当中的人 同样出自此处,不再注出),这当然是一种审美与知性的冒险, 预测的落空,是进行同时代史研究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这种研究姿态表明了认识主体在具体、实际而流动的状况中进行选择、判断的高度紧张感,这一紧张感暗示着批评者内在于时代,就好像置身于长流里的石头,切身感受着河水的流动、砥砺、温度,它奔腾时的冲击力,或涓涓细流时亲密的爱抚,并且将自身的生命信息与能量传递给河流,以生命信息和精神能量的传递、集结与聚合来回应时代 也许以上两种研究姿态都不可或缺,但我心意中具备 同时代性 的文学批评,更多指向前者。
在方法上,这种文学批评试图在创作 可能性的萌芽状态 中预期未来 更好的途程 。 作为生活在历史当中的人,总是要谋求比现状更好的结果,并且觉得这种要求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样的期待会贯串研究过程的始终。那种认为还有更好的结果,试图在各种各样可能性的萌芽状态中绝不遗漏地寻找的欲望 ,构成了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活力之源。 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 (参照陈思和先生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我明知当时的创作至少在作家主观上并没有达到我所想象的程度,但我总是愿意把我认为这些创作中最有价值的因素说出来,能不能被作家们认同或有所得益并不重要,我始终认为文学评论家与作家本来就应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用不同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对同一个世界的看法。 陈思和:《笔走龙蛇》 新版后记 ,《笔走龙蛇》第424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5月),始终以建设性的态度,扩张、敞亮创作者在追求 艺术真实 的过程中原先构想的 微弱的影子 。下面这段陈世骧先生的话,最能见出我心目中,在 同时代 状态下,文学批评与创作的理想关联: 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 (引自陈世骧《 夏济安选集 序》,《陈世骧文存》第194、195,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同时代 的批评不同于文学史研究或处理历史人物,在后者的场合下,不妨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思考逻辑、历史贡献以及所处时代状况作全面的洞察与把握。然而, 同时代人 的立场,决定了我虽然作为一个评论者,但并不能占据后来者的优势,因了然文学史的脉络与人物的结局而自命 客观 、信心十足地褒扬贡献、指点欠缺。在下文的讨论中,尽管文学史脉络是我重要的倚借,但这只是为了标明小驴出场的独特性,预测其去向的丰富, 计划更好的途程 ;也期待这种未来的丰富性能够摇曳多姿,也惊喜于 预测的落空 。
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其实都是对生活发言,以 不同的方式回应着相同的境遇 。说到底,探讨同时代人的创作,既是追踪文学可能出现的 新变 因素,也是理解我们这代人的生命经验。我把本文的写作,理解为新的起点,和小驴等同代人一起招呼着上路,寂寞时高歌一曲解乏,同时也彼此负责而严肃地检点、提醒曾经走过的的弯路与脚下的坎坷,不断试错、不断总结经验,共同计划更好的途程
二 鬼魅叙事
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出版于2009年10月,内中收集了小驴初期的创作,在此 学习时代 ,小驴接续传统,搜集来路上散落的历史碎片,在为一个崭新的起点而摸索、准备。从小说的题材来看,抗战、解放、土改、反右、文革 几乎构成一幅庞大的现代史画卷。很多人会把新世纪的今天看作一个没有来历、横空出世的新天地,全球化的大门恍如阿里巴巴的咒语,一下子就向我们指明了黄金世界的前景。小驴不会这么想,他沉浸于陈旧往事,其中不乏晦暗的梦魇,他肯定明白自我的诞生无法割断与历史的血肉联系。从另一方面来说,小驴也试图借助历史题材来寄托个人的记忆与情怀,从而淡化理想与现实直接而尖锐的冲突,但这并不是保守,而是一个自我准备的阶段,那个在历史中诞生的自我,携带着其整理好的个人记忆、人道理想与批判能量,即将重回现实空间,而时代大潮的罅隙中的无奈与激愤,即将在小驴笔下排闼而来。
鬼节、鬼故事、和亡灵一起生活的老人、狗泪涂于人眼而能看见鬼的传说 小驴笔下的这些元素,自然可以联系到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传统的浸润,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暂且按下不展开;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大罪》、《少儿不宜》、《弥天》等篇中的鬼影幢幢。《大罪》中并没有鬼魂直接现身,但读者肯定会为故事中阴暗惨淡的背景所惊心。只有在一片迷离惝恍、阴阳莫辨的氛围中,我们才能揣测一个可能因分裂/分身所引发的悲剧;也只有在身份功能错乱、幻想与现实交织错综之下,在日常理性监视的状态下不得发泄的怨气才会寻获突破口刹那间喷薄冲出,就像《少儿不宜》中游离 心中突然涌出 想将典型包工头打扮的胖子 一把推下桥的冲动 ,这种冲动终于通过《大罪》中的小马而一朝实现
怪力乱神其实都映射着人间实况,我们也不妨勘察一下小驴鬼魅叙事的源头究竟连接着怎样一个世道。农村辛苦供养出来的大学生反倒不如 农民打个死工挣得多 (《少儿不宜》)、年轻情侣辛苦攒钱买房,未曾想所在地区被纳入高新区开发蓝图, 一夜之间,原来的首付还不够塞牙缝了 (《大罪》)、开发温泉之后,本地人却无力消费(《少儿不宜》) 无怪乎绝食中的祖父在亡故前留下 这个世界就要变了,只是你们不知道 的谶言(《弥天》),无怪乎年轻人一边喝酒一边骂娘 我们80后没法活了 (《大罪》),无怪乎游离心想 这真他妈什么世道 (《少儿不宜》)。小驴的这些作品聚焦的正是这样一批与发展时代相疏离的青年群体,在日益膨胀的社会消费面前,他们被鼓荡起强烈的做 人 欲望,却由于社会地位的渺小与无助,摒弃在既得利益集团之外,也无力与坚固的社会结构正面抗衡,于是积怨与冲动,发为鬼魅幽魂,就像《大罪》结尾时, 从走廊里贯穿过来的风一阵比一阵的阴冷 ,烟雾萦绕中, 依稀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从走廊尽头走来 ,这是 人影 抑或小马化作孤鬼现身?读者这才想起小说第一节里小马曾 用力地拍了拍陈乘的肩膀,笑了笑说,早点修成正果吧,可别像我孤魂野鬼一个,死了没人晓得! ,竟是预埋的伏笔一语成谶。
正义与公理残缺,天地秩序摇摇欲坠,挣扎在社会边缘的人们艰于呼吸视听,于是种种逾越情理的力量四下蔓延, 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 (冯梦龙:《喻世明言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小驴似乎带着读者重回鲁迅笔下的阴森世界:吃人盛宴(《狂人日记》);死后冷笑的尸体(《孤独者》); 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魆魆的挺立着,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 (《白光》); 门幕一掀 女吊出场: 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 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 (《女吊》)愁云惨雾、死亡的蛊惑、复仇的主题、对世相的讽喻 小驴笔下的鬼魅叙事确实可以与鲁迅的文学世界相沟通。比如《少儿不宜》中的那条蛇, 蛇的肌肤冰冷异常,他感到皮肤像是要开裂了,血液溢出,全身痉挛,以至于打了一个冷战。但是很快就适应了过来,那蛇不紧不慢地缠在他的手臂上,身上的花纹烂漫无比。游离试着用鼻尖碰了碰蛇身,凉凉的 ,主人公游离与蛇显然具备某种神秘的呼应。我们当记得鲁迅的《墓碣文》: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早有学者将 游魂 解作鲁迅 第二自我 的化身。这其中的对应与转化也启发我们去理解《少儿不宜》,结尾处蛇被打死,游离 飞向陌生的南方城市 ,似乎是过往终结而开始新生,但我们切莫忘了游离临走前的一番作为, 火光冒起几丈高,南岳庙顿时成了人间炼狱 ,难道这里没有鲁迅笔下《长明灯》中那位疯子 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 , 仿佛想要寻火种 ,因为 我放火! 的影子吗?由此再来看游离为自己设想的 云游四方,不娶妻,不生子,不建房,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用去想,就这么晃荡来,晃荡去 的姿态,这究竟是 狂人 治愈,还是游魂重临?
鬼魅叙事的贡献还在于,往往召唤出潜藏在历史大叙述之下的记忆暗流,恍如幽灵一般,呈现 不可见物的隐秘的和难以把握的可见性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2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比如说小驴的近作《没伞的孩子跑得快》,小说碰触的是当代中国的话语禁忌,小驴之所以不想让这一历史事件因为被赋予禁忌色彩而成为一代人的 意义黑洞 ,可能是觉得 80后 尽管并不是直接当事者,但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态度所遗留的症结其实很难彻底消除。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自我主体的想象、甚或今天依然身陷其中的价值困境,未必不和当初相关,尽管当年只是不涉世的旁观者。在当下世俗社会与日渐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往的有生机、有意义的价值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公共生活和文化社群割裂,在外部一个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世界面前被暴露为孤零零的原子个人。当下青年人创作中一再出现单薄、狭隘、没有回旋空间的个人形象,与当年知识分子广场意识与启蒙精神膨胀到极点的溃败后,再无法凝聚起批判能量,未必没有关联。通过《没伞的孩子跑得快》,我终于看到青年作家直视历史暗角、梳理重大历史事件在自己身上的烙印。但这还不是我偏爱这个作品的主要原因,因为题材的选择并不能决定文学成败。1989年春夏之交,我正好跟随父母在北京旅游,完全懵懂,根本嗅不出什么特殊的气息,当时对于那个事件的所有印象,只是来自回家后看电视,以及父母的交谈(有同事的子女出事,母亲再三感慨)。没有历史感是可惜的,但我发现有的作品在表现时,往往将日后充分的 后见之明 (一个对历史的发展脉络 胸有成竹 的后来者)代入当时的形象,这就不能真切地表现人对历史的参与。我感觉《没伞的孩子跑得快》有种 最初的发现 在里面,或者说,那个孩子的视角在成长现场的实感保持得非常好,也许这和我自己对事件的感知正好吻合了。我喜欢这个作品的原因就在这里,当小驴在探视记忆暗流之时,既体现了历史感,又把握了艺术的分寸感。
我把小驴的写作理解为鬼魅叙事,还有第三层意思。在今天,全球化与发展的单面指标已经构成了一个巨无霸式的板块结构,迅速把社会推向超稳定的表象繁荣,同时有力地掩盖住内部所包容的各种混乱与矛盾冲突,很多年前,E.B.怀特曾感慨道: 某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人们本可以从他们的窗户看见真实的东西,但是人们却偏偏愿意在荧光屏上去看它的影像。 (引自威廉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第265页,杨照明、艾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这个 划时代的转折点 显然就是指 现代 的到来;而 荧光屏上 的 影像 恰类似于社会的表面繁荣与无数信息泡沫构造成的铁幕,让我们无法想象铁幕下还有人困于 蛛网 般 《大罪》中反复出现蛛网的意象,让人想起穆旦的诗句: 生活蛛丝相交,/我就镌结在那个网上,/左右绊住 (《有别》) 的真实痛苦。久处这样的境遇,人很容易变得麻木,其实《少儿不宜》已经勾勒过这幅景象 贵州妹无辜被害,但死亡与苦难无法引起任何人情伦理( 死者家里大概之前也知道她从事那方面的事,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样面子上难堪,他们平静而冷淡地处理完丧事,将死者安葬在靠南岳庙的河边便回去了。 )、社会秩序(警方将这桩刑事案 最后草草结案了事 )的反应与波动。今天这个时代,写作的高下就看其与上述 荧光屏 、铁幕构成何种关系。或者是被彻底压服,无法感知他人甚至切身的痛楚,竟而虚造出不受市场资本、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制约的 自由状态 (这种状态很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宽容与支持),甚至是 坐稳了奴隶 的洋洋自得。当然还有另一种写作,饱含着难以排遣的孤独感、自身精神上的失败感,与 荧光屏 、铁幕以及主流的全球化板块分离开来,就像 游离 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种格格不入与疏离抑郁,完全成为精神旷野上的 孤魂野鬼 。在中国传统民间社会, 人 死后进入阴间的 鬼 ,一般分为两类(参见丸尾常喜:《 人 与 鬼 的纠葛 鲁迅小说论析》第8、9、219、220页,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一类得到子孙祭祀,同时作为对其供养的回报,保佑阳间子孙的生活平安,其实已具备与 神 相近的品格;另一类则因为没有后嗣 如生前为未婚姑娘或被夫家休弃的女子 而不能获得祭祀,在阴间得不到安定的生活,徘徊游荡于阴阳两界的边缘,冤死者甚或肆虐复仇,这一类即 孤魂野鬼 ,他们被种种血缘的、宗法的、父制的共同体所排斥。引入本文论题,我所理解的鬼魅叙事,不仅是指内容上的怪力乱神,还需要具备小驴创作所暗示的那种精神气质 将东游西荡不驯服的姿态、 我要的,全没了,我不想要的,全来了 的愤懑呐喊(《少儿不宜》)、以及放把火烧光这人间炼狱的发泄,曲曲折折地转化成艺术审美,终而发为 真的恶声 。
三 焦虑感,及 青春文学 的再生
据沈兼士考订(引自沈兼士《 鬼 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国学季刊》五卷三号,19 5年。此据《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86~202页,中华书局1986年12月),人死为鬼,虽为一般的传统解释,并延及今日,但 鬼 之原始意义, 疑乃古代一种类人之动物 , 自其性质之黠巧引申之,则为诡,为谲 。不管是初起的 类人之动物 ,或后发的鬼神妖怪、人死后的灵魂, 鬼 都保留着奇谲、敏慧、 常人 所不具的才能。鲁迅对神秘阴森世界的抵拒与迷恋,在 五四 新文化一片清明而理性的光照下,特别显出意味深长。 天未明时有幢幢的鬼影,阴森的细语和其他飘忽的幻象。这些东西在不耐烦地等待黎明时极易被忽视。鲁迅即是此时此刻的史家,他以清晰的眼光和精深的感触来描写 (引自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夏济安选集》第2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正是因为在光明与黑暗间徘徊无依的姿态,以及常人不具的 清晰的眼光 (许是得自鬼眼的 第二视力 吧),鲁迅才能洞察生活和文学的秘密: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 意图 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 美 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 (引自鲁迅《漫与》,《鲁迅全集》第6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当别人急于粉饰黎明后的黄金世界,或 安住于这生活 之时,鲁迅却从中隔绝出来, 彷徨于无地
在今天的青年作家笔下,见惯了 平安 的文学,殊少 不安 的文学。我喜欢小驴的小说,最大的原因正在于,从他的文字里,我扑面感受到一种无时或已、万难将息的焦虑感。为了说明 焦虑感 的独特性,我想有必要做一些文学史的回溯,关注文学中的青年人形象以及青年文学生成、转变的轨迹。这是一个大题目,暂且从1990年代说起。
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空间的日益开放,文化的 共名 状态(关于共名与无名的理论阐释,及由此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考察,参见陈思和:《共名与无名》,《陈思和自选集》第1 9~15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逐渐涣散,为那种更偏重个人性、多元化的 无名 状态所取代,在创作上则体现为个人叙事立场的转型,此时, 十七年 、 文革 成长小说赖以建立文本的理念底蕴 个体成长的意义象征国家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须臾不可分割、个体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人质 这样的文本立意基本上崩解了。个体成长的最重要的关系空间不再是国家,而是具有初步自律功能的社会。这样,个体获得了他所能期求的最低限度的理想成长状态 自然状态 (引自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第22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 年12月)。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使人们看到了青年运动的代价和边界,年轻人由此从社会得到了摆脱 神圣使命 约束的某种默许和认可,放下了角色扮演的包袱。总之,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个人叙事立场的支持、以及青年从 救世主 的幻想中获得解放,这一切,都促使青年文学逐渐告别宏大叙事转而开拓个人心理空间和主体经验。在这方面,以朱文、韩东为代表的一批被称为 新生代 的青年作家和卫慧、棉棉等 70后 作家作出了贡献。
及至新世纪情形又发生转变。按照王晓明先生的分析,今天的中国人 同时受制于三个社会系统 : 第一个是国家机器主导的政治系统,它以 维稳 为宗旨,竭力加固那种 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 的普遍意识。第二个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它通过各种具体的成文和不成文法,持续训练人接受这样的自我定位, 现代人,就是如下两面的结合:合乎市场需求的劳动力,和具有不可控制的消费冲动的消费者 。第三个日常生活系统,它安排人以 居家 为中心,组织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内容,从儿童时代接受学校教育开始,一直到老。这个系统持续地发展一种具有极宽的包含力的 居家文化 ,对人潜移默化,要将他造得除了 居家 的舒适 当然,这里的 家 并不仅限于小家庭和公寓范围 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王晓明、王侃:《三足怪物、叛徒、谜底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在这三个系统组成的支配性文化和意识形态笼罩下,青年人往往具备根深蒂固的实用理性,对自己选择的价值观秉持类乎 历史终结 般的坚信,戒绝任何越轨的冲动 于是,1990年代文学中自居于主流和世俗社会边缘、苦苦寻求自我精神拯救的青年人(如朱文笔下的小丁们)、以 裸的笔墨挑战 所谓致富阶级(成功人士)温情脉脉的伦理规范 (陈思和:《现代都市社会的 欲望 文本 以卫慧和棉棉的创作为例》,《谈虎谈兔》第2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的叛逃者(如棉棉、卫慧笔下的女孩子)全都消失了。其实这两类形象的消失有迹可循,有论者极富创见地提出了 终止焦虑 这一考察视角:焦虑是通过与现实处境持续的紧张对峙来艰难摸索一种自我确立的主体力量, 焦虑感是作家主体通过文字与世界发生关联时承受的障碍所致,是心灵的想象与现实境况相互磨蚀的结果,在有些情况下正是人不放弃追求主体力量的证明 。差异正在于,朱文 同样表现 无所作为 的虚无感,但深刻地描绘了写作者的内心焦虑,毫不放松地突出着对主体力量的渴望 ;而到了卫慧、棉棉等 70后 作家笔下, 主体在对现实的反应中自主性明显弱化,认同感逐渐增强,两者的关系处于相互整合之中,而不是主体自觉疏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个体存在 (引自宋明炜《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 关于70年代出生作家的笔记》,《上海文学》1999年9月)。到了新世纪,明显反映出这一 整合 过程完成、连摩擦痕迹都不复存在的,是青春文学中的两类青年形象。
一类是郭敬明式的小说中 拒绝成长 的 孩子 ,其最显著的特征即 主人公的静止不变 : 对个体的忧伤、创痛的反复咀嚼不仅成为文本推进的主要线索,更被普遍化为某种本质的、从来如此的青春体验,这一操作的痕迹最为鲜明地体现在郭敬明对 孩子 这一概念的反复言说之中。在郭敬明笔下, 孩子 不仅是一个年龄阶段,更是一个可以脱离各种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绝对纯洁的领域, 孩子 这一范畴成功抹去了个体的创伤与其社会根源之间的关联,从而建构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主体。对于这样一个主体而言,由于无法在具体的社会结构、生活经验,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中辨析创伤的来源。因此,他只能将其视为本质的、普遍的青春忧伤而加以领受,甚至将其审美化,并反复观看、咀嚼。同时,正是这种将自身独立于社会的意识形态构型,询唤出了大量自我封闭的、拒绝成长的主体,取消了任何对抗性实践的可能性,从而不断再生产着既存体制下的权力关系。 (引自康凌《林道静在21世纪》,《文学报》2012年2月9日)无须让生命悸动的痛感来提醒自己,也无须在黑暗的长旅中左冲右突,铺天盖地的广告、传媒早已告诉了那个 孩子 成人世界的秘密与真相。郭敬明笔下这个 只想呆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 ,以持守纯真的自恋姿态来暗享 豁免权 (当 抄袭 事件闹到法庭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记者问及郭敬明是否在意,郭的解释是: 我不想参与到成人世界的争斗中,我只想呆在自己的世界里。 );同时又在早已熟稔成人社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将成长过程 压缩 ,一出场就 定型 。从表面上看,这个 孩子 的形象刻意呈现出一种 中性 (去意识形态化、去精英化)化的生活姿态,这种姿态很容易俘获大批读者,但很明显恰恰受制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衣食住行背后是对市场社会主流价值全面认同。郭敬明笔下的年轻主人公、他提供给年轻读者的范本大抵就是成功人士的后备军,而成功人士恰恰是当年朱文、棉棉们曾试图挑战的对象。这是时代精神现象的表征:当下是一个 诸神归位 的时代,对于年轻人来说,选择哪条路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挤掉多少人、超过多少人。举目所见都是价值观稳固、静态而不再成长的 孩子 ,而绝少村上春树所谓 可变的存在 ,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尚未牢固确立 , 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 (引自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 中文版序言 ,收入《海边的卡夫卡》,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7月)。其实文学史上真正拨动人心弦的,反倒是后者那些在生存环境中左冲右突而又无所归依的 边缘人 ,他们才能提供 可能性 ,比如鲁迅笔下的孤独者、郁达夫笔下的 零余人 、张承志《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朱文小说里的穷酸书生、甚至贾樟柯电影里游手好闲的小武们
今天文学中的另一类青年形象,是平抑了欲望,甚至消解了绝望后,外表淡漠、心如死水的人。有位年轻的研究者作过这样一番观察: 欲望,在我们以往的文学作品里多是人物行动最根本的动力,且从未有这样一些对它丧失兴味的正常人,而且是青年人。张悦然《一千零一个夜晚》正是写出了由禁欲时代之后诞生的一代青年人,他们因过分容易的欲望满足,而逐渐丧失欲望兴趣。 在一个表面更加自由、富裕的世界里,这些物质条件优渥的青年人已经到了他们生命旅程的悬崖边 (引自李一语,出自金理、李一:《新世纪青春小说:期待 逆袭 品格的重生》,这是《新世纪十年小说大系》 青春卷 的序言,该丛书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之所以外表淡漠、心如死水,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除了 物质条件优渥 之外,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根源。在今天这个 表面更加自由、富裕的世界里 ,让年轻人糟心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方圆几公里都找不到一个励志故事 (韩寒语),如果 睁了眼看 ,无奈、无力甚至绝望感可能每天都会侵扰你。问题是,我们大多已经找到了游离、化解的渠道,王小妮在《上课记》中的一番记录,告诉我们达观而犬儒的青年人是如何炼成的: 我渐渐发现在他们的内心和现实之间留有一个空间,一个缓冲带,他们早适应了在自我和现实间随意游离,那是一条由生物本能和现实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切换通道。他们学会了在多种不同的立场观念角度间凭着惯性自如转换,不留痕迹,毫无尴尬、勉强和被迫,他们也由此得到保护,避免内心的痛苦纠结。 他们游移藏身在这个弹性无限的空隙里,灵活转身,呈现自己的多面性,从而获得安全感,使他们的犬儒境界自然而然地享受快乐而达观的宽度。上一代人与现实之间形成的某些如芒如刺的感受,几乎被他们化解干净了。 (引自王小妮《上课记》第1 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12月)日本学者千野拓政教授近年来致力于考察东亚跨国跨社会共通存在的精神现象、青年人共有的精神状态等问题。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及:日本政府近四十年来每年进行《有关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以及《有关社会意的舆论调查》,在调查中,被问到 是否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 时,回答 满意现在的生活 的年轻人2010年最多,在20 29岁年轻人中,男性占65.9%,女性占75.2%。这一代年轻人被称为 达观世代 ,出生于1980年代之后,他们 不开车,不想要名牌衣服、不做运动、不喝酒、对恋爱也很冷淡 , 社会的闭塞感不断增强,即使抱有梦想和目标,能否实现也无法确定 ,由于 在事前就会早早预测自己的行动会带来什么结果 ,于是 没有过高的期待和要求 (引自古田真梨子《达观世代没有欲望的年轻人》,《新鲜日本》第11 期)。日本社会学家这样分析此现象: 对将来还留下可能性的人,或者对以后的人生还持有 希望 的人回答 现在我不幸福 ,不算否定自己 反过来说,当感到自己不会更幸福的时候,人只好回答 现在我幸福 。 这位社会学家的研究报告题为《绝望国家的幸福青年》(引自千野拓政、吴岚:《文学的 疗救 、纯文学、轻小说》,即将刊于《中国图书评论》。这是笔者主持的 多重视野中的 80后 文学 研究计划中的一项成果)。只有那些觉得社会结构已经闭合,万难改变的青年人,才会认命,终于心平气和,选择 幸福感 ;相反,那些还有能力去想象一个更加理想、更加美好的生活世界的人,依然觉得改变当下是有可能性的人,才会焦灼、感到不满足。在今天的日本和中国,大多数人都选择前者。巴赫金说: 强烈感觉到可能存在完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绝不同于现今实有的生活和世界观(并清晰而敏锐地意识到) 这是小说塑造现今生活形象的一个前提。 (引自巴赫金《关于福楼拜》,《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第98页,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正因为我们已经弃绝了 完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 的想象力,所以今天青年文学中才出现那么多匍匐、疲沓而逼仄的人物形象。这是文学性质与社会语境的交汇点:文学应该启示的是一个 异质的世界 ,它打动的是那些不安分的人,与现在的境况构成某种紧张与对峙,由此产生焦虑感, 现在我不幸福 ,但恰恰 不算否定自己 ,而是追求 更理想的自己 。但是,当这样的一种文学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 无法启示更大的世界,很难投入感情,因而无法产生接触到真实的感觉 之后,年轻的读者只能驻足于郭敬明的 小时代 中,或想方设法避免内心的痛苦纠结,渐渐地 不留痕迹,毫无尴尬、勉强和被迫 ,最终放弃对更好世界的想象,借上引鲁迅的话 安住于这生活 。
以上两类当下文学中常见的青年人形象,都已经克服、告别焦虑感,将 与现实之间形成的某些如芒如刺的感受 化解干净 ,也许这正意味着一种带有先锋性质的青年文学的离去。我们正处于绝望后的一片死寂中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死寂中,有必要重访鲁迅的 铁屋子 :曾经一度清醒、天真的个人,当面对 万难破毁 的困境,是否只有一种选择 重新安排自己进入原先的世界,从 昏睡入死灭 ;抑或辩证对待必然性与能动性, 有没有可能,通过有目的性的活动,来逃脱那囚禁我们的社会历史结构 ?(引自安德鲁 琼斯:《鲁迅及其晚晴进化模式的历险小说》,王敦、李之华译,《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2期)自然,人无法绝对 自由成长 ,按照福柯的说法,主体是被 规训 出来的,在被规训的环境中,是否可以 能动的生成 个体在构造客观性活动的过程中,以独立的个性理解世界的经验存在,进而以一种积极探索与突破的精神重构世界(生活世界、科学世界或哲学世界)的秩序,最后完成了独一无二的生命存在史 ?(引自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第257页)我们切莫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 诞生之作 《狂人日记》讲述的就是一个能动主体临世的故事。同样我们不要忘了,狂人并无固定的职业,也谈不上成熟的思想体系,年龄约在三十多岁(根据小说开篇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 可以大致推定),这是一个青年反抗者形象(在 从来如此,便对么 的质问中,现代青年的反抗者形象在文学史上登场:狂人、觉慧、蒋纯祖 );《狂人日记》是一部典型的拥有成长主题的青春文学。而青春文学自来就具备先锋性质(引自对 五四 新文化运动先锋性质的论述,参见陈思和:《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收入氏著《海藻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现代文学史上的青春文学和他们的创造者们,同样身处主导性文化的严密限制之中,但却通过足够强大的艺术才能、 绝望中抗战 的勇气、韧性的战斗精神,创造出 冲决罗网 的文学空间。
我最近翻一本在年轻读者群中比较有市场的主题书,那一期的主题是 文艺青年 ,编者认为 文艺青年 有两个特征:一是封闭性, 精神世界是完全封闭的 ,对现实生活很淡漠;二是自足性, 对现状总能苦中作乐 ,善于自我安慰,说服自己 慈眉善目地打量这个世界 。这是今天语境中对 文艺青年 的理解,这位编辑显然不理解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 文学青年 是怎样一拨人:他们不安分,与周围环境构成紧张的对峙,喜欢跟坚硬的墙撞一撞,总在尝试表达超越性的诉求,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为自我争取更多选择的可能,也愿意为此付出冒险的代价,投身未知的领域。这位编辑想必也没有读过路翎
从强烈的快感突然堕进痛灼的悲凉,从兴奋堕到沮丧,又从沮丧回到兴奋,年轻的生命好象浪潮。这一切激荡没有什么显著的理由,只是他们需要如此;他们在心里作着对这个世界的最初的,最灼痛的思索,永远觉得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呼唤。
他每天都迷失,他似乎是在渴望,并追求迷失,他每次都冲了出来。黑暗的波涛淹没了一切,他只在最后的一点上猛烈地撑拒着。 (引自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478、479、10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月)
这是蒋纯祖,路翎笔下的 文学青年 。在世界 那个 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 的世界 面前,永远跃动着强旺而新鲜的感受力; 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 ;永不停息地抗辩客观世界中既成、稳固的绝对原则;并将上述感受、抗辩落实为美学创新,这种创新可能免不了粗糙、芜杂,但它镌刻着年轻人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这一探索是诚恳的、运动着的, 艺术上的搏斗都燃烧在青春底熊熊的热情火焰里面 。(引自胡风《财主底儿女们 序》,《财主底儿女们》第1、7页) 在这个意义上,《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部 青春底诗 。
将郑小驴的创作接续到文学史的脉络中,是为了召唤一种青春文学在今天的重生;小驴从这个接力点开始跋涉,在无边的旷野上,他即将和蒋纯祖们相遇
201 年5月7日初稿,5月8日改定
金理,1981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批评家,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
- 12-29[奇幻]甄嬛传:果郡王其实知不知道双生子是他的?你看他回京时见了谁?
- 11-16[奇幻]西藏矿业现1笔大宗交易 总共成交442.27万元
- 11-15[奇幻]谷爱凌的战斗力,有一半竟然是因为这两滚头发?
- 11-14[奇幻]装修,别抱“侥幸心理”,避开这6个点,要新颖更得安全
- 11-11[奇幻]马斯克拜师了张小龙吗?
- 11-07[奇幻]别等装修结束,才去付钱家电,这4种最好提前考虑,不然麻烦都你的
- 10-22[奇幻]40集悬疑剧《杠杆》刚才开播,郭京飞领衔,3大看点,有爆款潜质
- 10-17[奇幻]广州今年继续实施1+3培养试验,41所学校计划招生3258人
- 10-13[奇幻]债权人远程赋“红码”被针对?相关单位:对不起,大数据出错了
- 10-12[奇幻]为何老一辈说黄鼠狼不能杀?科学研究表现,原来是不是不能杀
- 10-11[奇幻]停下来核酸手上盖章并保持3天?街道道歉
- 10-06[奇幻]衣服存放小技巧,一年不返潮不长虫,有点管用啦
- 10-03[奇幻]德国4月初PPI同比上涨33.5% 因能源价格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