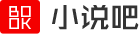一四老汉的故事br高邻李木四离开
一四老汉的故事
高邻李木四,俗称四老汉,身材魁伟,体格健壮,一看就是块当兵的好料。的确如此,李木四出现的时候,总爱唠叨:“社会都好成啥样了,你们还不知足?”
不知足,对,也不对。我们只是羡慕他的儿能折腾,在外不知干啥营生,每次回来都西装革履的,总拎着一沓拾元大钞在人前一五一十地数着。
李木四对此不哼不哈,毫不在意。总在讲他的古经:“我八岁的时候就给地主家放羊来着,起早贪黑的还吃不饱。你们多享福,小小年纪就上了学堂,识文断字,没有人敢欺侮。”
“哼,谁信,我大又没有说过!”围观的小孩子觉得没意思,就走散了。(大,是爹,父亲的意思,陕西关中方言。今天,官称父亲为爸爸,方言则为爸,简洁了许多。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叫爸是在外公干人家的标志,而叫大则是农家出身的标志。)四老汉变忙乎他的本业去了。
他的本业是啥?石匠,是也不是。他看起来年纪较大,四方大脸,白白胖胖,赶牛拉纤的似乎有些笨拙,队长应该是觉得他有高血压,老是照顾他。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没有被作为生产队耕作劳动的主力,即使是在火热的农田基建运动中,也很少见他的身影。他出现在人群中,也总是这样说道:“你看那县城阔的,马路开阔,楼房林里,一街两行的小伙衬衫白净,姑娘裙子招摇。新修的石桥,条石四棱界线,几个人都抬不起抱不动,吊车装上去的。”
“那你为啥还去卖你的条石?还不担子挑了倒到沟里去!”
“我那条石,个儿虽小,铺不了地,搭不了桥,但是人们都希投这买。”
“为啥?”
“因为那没有咱这么好的石头当磨石,磨刀启剪子,磨镰开刃子,都需要我挑去的磨石,懂不?”四老汉自豪地说:“卖完磨石,总共一块五毛钱,五毛钱咥一碗羊肉煮馍,还有余头,跟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强得多哩!”
“屁,不信。”我想:“自家巴掌大的条石一大摞,挑来拣去没一个中用的;况且门口那块大立石都磨出弯来,也不见扔的。你那就有多好?好,县长咋不征去搭桥?”后来才知道,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县西的老百姓就是需要这样的石头做磨石;他们那儿不出产这个,全村只有四老汉一个人不惜力气把石头担出去卖,因此好歹也没个捡头,包圆售罄。
那条石的确没啥稀奇的,只不过是开采石方的边角料而已。东沟喇嘛岩下泉水四溢,石层高耸,原始的开采方式就是找一个合适的缝隙把火药雷管装进去,用引线引燃雷管爆炸炸开石层,得到整块的石方。但是缺少经验,炸出来的石方不够平整,甚至碎石遍地,凿子錾子等都搭不上去。四老汉就是有经验的人,在亦农、亦商、亦木、亦牧、亦石匠的自由生产的解放前,他可称得上一个多面手,简直就是大师级人物。据说走到一个石层前,他略么思量,就可以断定这处石层的长宽高深;哪处匣药合适;而且布药量的的大小,雷管的个数,引线的长短,点火的时机;开采的石方,可以分割开凿成几副石槽档和石槽头,够不够一套石槽;够不够开凿出巨大浑圆结实的碌碡;够不够凿成内圆外方的巨大的又薄又平窖口石;剩下的石料,能凿成门墩呢,还是能凿成砸辣子窝窝,凿成砸蒜窝窝,石炕边沿,镇风箱的盖子,瓮盖子,石窗台,门下石,还是能凿成猪食槽,石台阶,石凳子,等等,他都算得一清二楚。而且开采成料器具出齐,一件一件摆齐整,也几乎不差一二。村民后辈,凡是干石匠这一行的,都很敬重他。他也因为常炸石头抡铁锤挥凿子,耳朵背,人们戏称他为四聋子;饭量大,一顿饭吃过十海碗的干面条,赛过了远近闻名的吃饸饹吃八碗的八老碗。
“考试考咋样?”四老汉又来了。
“不咋样!”
“不咋样就对啦!”四老汉一本正经地说:“给你们讲,老早有个老农听说来了个新县老爷,是新科的状元,当朝的驸马,就背着他的行头来到县衙大堂。对县老爷说,老爷的学问大,草民有些事不明白想麻烦问一下。说着摆出了他的一副行头,问县老爷认识不?县老爷说认识。他问认识,你说这东西前面的这叫啥,后面的那叫啥。县老爷张口结舌,眼睛瞪得生大,尴尬的啥都答不出来果然把状元驸马给考住了。你知道,他的那套行头是啥?”
群童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不知就里。
“看把你们这些文明人考住了么?告诉你们,他拿了一副套牲口拉犁拉车的那龙套,前面弯的叫牛跟头,后边的横木叫曳弧子,两头连的叫缆绳,中间的短绳子叫肚带。记着吧,以后考大学的时候问一问监考官,弄不好不用答题就能上大学哩。”
大家一听,觉着好笑,你个文盲知道个啥,甭看我们年龄小,我们可不好哄,不念书还想上大学,连门都没有。不读书,没文化,连家里蹲大学都上不上,连犁把大学都上不上,你闲着没事干去打牛后半截去吧。
回去把这一段给大叙说一番,大说:“你四爷和你们说笑呢。他过去得罪过土匪,在泾三原失手打死了曾到村里抢劫的土匪,被人家找上门来报复。幸亏他发觉早,躲进了洞子沟。也是你五伯面子大,给人及赔了钱赔了枪,才最终息事宁人。不信,你见了去问他这等事。”
五伯大大的个子,瘦瘦的身材,清癯的容貌,见人不声不哈内敛非常。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叫耙娃,倒是非常咋哇,爱与人斗嘴论高低。生了个儿子叫国勇,一眼大一眼小,后来学的医生,还是个半眯——不太通。住的宅子叫老屋里,据说成分是地主,搞运动的时候挨过斗。不过老屋里那偌大的宅院现在已没有几间房子,狭窄的庭院仅剩的几间青石铺路的高大瓦房在诉说着昔日的奢华与尊荣。
有一天放学回来,大家又聚在一起,商讨对付四老汉的事。恰好李木四下地回来,肩上横着铁锹,老远看到我们,就往孩子群里凑,嘴里嘟囔着酸溜溜的话语:“哎哎哎,还没到吃饭时间里,一个个洋学生都逃回家了,不知道在学堂里多读会书,看把你大你妈在地里都累成啥样啦?”
“累成啥样也不用你管!”年龄不大不小处在中间地位的快嘴何姐说:“那比谁躲着挨枪子强得多。四爷,你见那人了么?”
四老汉一听话头不对,放下铁锹来拄在怀里,道:“说啥哩,瓜蛋娃知道个啥?我扛枪那会,你大和你妈还没认识哩,你们不知都到哪里呢?”
“你扛过枪,在蹦吹了,看把天给吹塌了。”
“吹哩,不信你们到村子打听打听,县城解放那会我给八路扛过机枪,与国民党梁干乔在爷台山干过仗。那场面给你说把你们都能吓死,子弹在头顶嗖嗖飞,近的都能擦破脸皮,脚底下尘土拿机枪子弹扫起老高……”
“你不言语,就跑啦!”
“喝,说的那傻话!跑,给你十个胆,八路军优待俘虏,却不轻饶逃兵,看不一枪把你给崩了,那纪律严明的太!再说,打仗谁敢胡思乱想,该打就打,该冲就冲,你得随着大部队,一不留神,脑子跑了毛,那就挨了飞子,小命就没了。”
“那人家国家给老干部平反,加工资,咋没听说把你给捞上呢?”快嘴何姐说。
“瓜娃,知道的还挺多。”四老汉说着,把怀里的铁锨往前一扬:“快了,我跟县长谈了一大晌,临走他把我都送出门来。县长忙啊!”
“四爷打仗的事还没讲完呢,你咋就走了?”
“留一点酵头,等下次吧,大伙都是忙人。”四爷说着扬起铁锨望肩上一送,奔家里走去,我们也各自往家赶,因为吃过午饭下午还要上学呢。
四爷确实当过兵,这还是从父亲那里证实的。但是,他到底是给共产党扛枪呢,还是给国民党服务,谁也弄不清。因为当年打仗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想办法躲得远远地,各自保命,本地做人的观念就有一条“闲事甭管,打捶(架)列(离)远”的古训。我想那些个胆大的,二杆子之类的才往前凑,要么就是被抓壮丁,够惨的了。
“那咋没人给四爷作证?”
大说:“没人,战场离村里远,打仗是好玩的么?要死人的!仗没打完,是散是逃,谁也不知道?临时的兵,审来审去,政府也搞不清。”
“那他还寻啥?”
“要待遇呗!人家抗美援朝,反击印度,回来的兵,国家都给补贴。可惜呀,他们没给捞上。”
“他们,还有谁?”
“你志东哥和你清亮爷。”大说:“他动员人家找政府,人家还不去呢。”
志东哥和清亮爷都是本村的近支,虽已年过半百,爱枪似乎是他们的天性。家里都有土枪,闲时装上火药、砂子,大大野兔、野鸡什么的,枪声一响,引来娃娃群铺天盖地的围观。他们不寻,大概是不稀罕那几个钱吧;但据说他们竟然连枪都没摸到,就给吓跑了,当年清查白军残余的时候,好心的乡亲作了隐瞒。是白是红,自己心知肚明,难怪四爷跑前跑后辛苦的寻前程,他们总缩着不动……
二婚姻变奏曲
“娃呀,给你说个媳妇,咋样?”四老太调皮地说。
“我不想要,年龄还小,书还没读出来哩!”
“都十三四岁了,还小?我十一岁添的你大姨,十四岁和你四爷结的婚。”
“不嫌丢人,你把这事还给人说哩。”
“啊呀呀,我给说反了。我十一岁和你四爷结的婚,十四岁添的你大姨。”四老太臊了个大红脸,改口道:“说个媳妇,又不影响读书。北边山上我家亲戚,家里盖两层楼,有个女子十三四,虽不念书了,但人勤快,浓眉大眼,白白胖胖身体好,没啥病形。娶回家,给你做饭忙家务,把你大你妈不是解放了。”
“去去去,都啥年代了,哪能像你当年那一套?”我没好气的说,“趁李木四不在,赶紧把你给卖了,省得人家不高兴,丢(抓的意思)住你的帽辫子(即辫子),把你压到地上跟实施工地全部停工、强化道路吸扫冲刷频次等措施捶猪似的,让人听见你鬼哭狼嚎的。”
“这瓜娃,给你说媳妇哩,你咋截你四婆短哩,简直瓜得实腾腾的。跟你不说了,我忙去呀!”
“忙去吧,头上戴帕帕,走东家串西家,有啥正经事嘛!”我送她一句,继续割自己的猪草。
四老太挨打,并不是常有的事,她是个灵醒(聪明)人。那次,生产队收工后,三老太和四老太妯娌两个回家做饭。不知是老三家的鸡啄了老四家的菜,还是老四家的猪拱了老三家的院,俩老太一边生火做饭,一边没好气地嘟嘟囔囔。灶膛里的火越生越旺,双方的气也越生越大,终于有一方憋不住一下蹦到了院子,另一方也离开灶房来应战,这样高一声低一声的,地窑院场上周围都听得见。
李木三拐着腿,紧三火四地奔下院子,瞅瞅这个,望望那个,摩挲双手,不知该拦挡哪一个。只好咳声叹气,蹲在院子当间的渗井盖上呼呼喘气,嘴里不停地叹道:“好我的先人哩,咋不嫌丢人哩,吵个不停可咋办呀?”
“甭吼啦!麻婆娘(仿佛泼妇那样骂人的话)。”一声晴天霹雳,原来是李木四回来了。他一手拽了三老太一个领口子摔在当院,一手抓了四老太的麻雀辫子摔在脚下。三老太见势不妙,爬起来掸掸土,灰溜溜地窜进厨房做饭去了。四老太吱哇一声,辩解道:“她先骂我来,你却打我哩。”李木四气不打一处来,拽着四老太的帽辫子拖死狗一样,把她推搡到坡坡头(出大门口,上到地窑院与公路相接的地方),摁倒跨到身上,脸上嘴上使劲扇了几下,疼得四老太赶紧告饶:“好我的碎大哩,不打得成,我错了还不行吗?”李木四也干脆,抖抖衣衫站在一旁吼道:“闲事婆娘,还不做饭去,吃了人还上地呀!你没事干吵架,想把老大饿死不成?”四老太一轱辘爬起来,土来不及掸,奔下场院去了。
李木四的儿子李来子是个不安分的主,最能折腾。高中毕业没事干,也不预算在生产队劳动,整天磨在我家里。大概因为和哥哥姐姐一起念书的缘故,有时帮着干这干那,常常吃饭也不沾自家。李木四在村院中数落自己的儿子,是“家懒外勤,邻家的好人”。我们也不好,我的父母也经常劝他回家去,他嘿嘿一笑说:“他说他的,哥嫂,没事,他们想把我管死哩,我偏不听,看他能咋样?”父母也没办法,人家不回去,咱也没办法,催得紧了,反倒显得我们小气,舍不得给人家吃似的。
但是,李来子后来却主动走了。一是哥哥姐姐都上了学,或者放羊,下地去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小妈一家搬了来,打水喂牛的活几乎被他全包了。小大(小爸)在县上的商业上坐办公室,据说安置了不少有一技之长的外地工匠,李来子眼真亮!的确,不光是“碎哥,碎嫂”不停地叫着的功劳吧,李来子被招到了矿上。由于他的人事活,后来又转到了矿上的商店,当起了体面地售货员。
然而,李来子的人事活得过了火,一次和几个朋友在县城的食堂喝酒,醉醺醺的,当街拦着碎大拽着他的衣袖“碎哥碎哥”的叫。碎大和领导上街公干,遇到这等事,当时既尴尬又生气,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不知如何是好,索性就给了李来子一巴掌,才算把他甩脱。
据说碎大回到办当我面对这些问题时公室,领导问碎大:“老尉呀,你啊还有个兄弟,人还能行得很!”
碎大知道领导话里有话:“主任,没有,我姓尉,他姓李,一个村的罢了,我咋能有这样的兄弟呢?”
后来呢,后来一查李来子的账目,真差的不少,直接被开销。他蔫了吧唧的回到村里,朝天日每的也跟着李木四扛钎破石,也跟着四老太下地干活,真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学起好来了。再说,他也二十好几,到了该娶媳妇生孩子的年龄了。可人家的好闺女早都出嫁了,剩下的他也瞧不上。于是,清河岸边的岸头村一家觉着这儿还不错,村上村下行走方便,交通便利,日子还好,愿意把女子嫁给李木四的儿子做媳妇。人娶过来,身体结实,白白胖胖,四方大脸,眼睛不大不小,人勤快淳朴,就是不太言语,大家都管她叫“琴英姨”。
共 10607 字 页 转到页 【编者按】“辣椒很红,姑婆的话很中听。”一个村子就是一个世界,村子里形形 的人上演着各自不同的故事。不惜力气把石头担出去卖的四老汉;四老汉家妯娌及儿子媳妇之间的关系;脾性挺大,家里没人敢惹的老胡;为了几句闲话跳窖的崖下娘……本文作者用亲切、朴实的语言塑造了一群性格不同,神态各异的主人公。正是这些似曾相识又各具特色的人们构成了大千世界,让我们的生活丰富饱满起来。作品语言简练流畅,取材贴近生活,生活气息浓厚。感谢赐稿,!【:海淼】【江山部精品推荐】
1楼文友: 21:50:09 拜读何心雨文友佳作,祝创作愉快,事事如意!
漯河治疗白癜风好的医院吴忠治疗白斑病费用
南充治疗白癜风方法
- 02-19[二次元]吹拉弹颂唱响曲(二)——观赏《往日国乐》两年情思小结
- 01-13[二次元]2022年焊工考试高级焊工考试梁汉文套卷及答案
- 12-28[二次元]FASHION 有料 | 6.23 时髦快讯
- 12-05[二次元]关乎大资金动向!科创板“芯片”指数来了,42只样本股名单公布;上交所几大指数也调整,腾讯、美团等权重
- 11-30[二次元]农发行阿坝州分行助力民营小微民营企业发展
- 11-28[二次元]又一富豪入驻!李兆基出手投资新加坡!
- 11-21[二次元]汪汪狗狗去郊游,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玩沙子 小孩子的快乐总是那么简单 陪伴孩子的美好时光 ;还有 工程车
- 11-19[二次元]贵阳温江区:契税缴纳“掌上办” 下沉服务获点赞
- 11-17[二次元]河南信阳:购房首付比重最低两成,买新房给予50%契税补贴
- 11-12[二次元]赠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海信空调为你健康护航
- 11-10[二次元]Polycom宝利通soundstation2基本型/标准型/引入型八爪鱼会议电话简要说明书
- 11-06[二次元]许诺我,这个夏天一定别错过“甜辣风”穿搭,清爽惹眼,很洋气
- 10-30[二次元]不应有!对阵塞尔比被狠批,金左手犯规不吹,颜丙涛进4强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