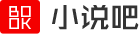扎西达娃的每一个文学创造(1)
摘要:扎西达娃的每一个文学创造,无不置于作家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之下,表现出鲜明的本体意志色彩,呈现出一如既往的理性思维定势。在他的世界中,“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规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作家始终不渝地朝着他既定的目标奋进。与当代文坛上的某些作家相比,在当代文学走向深入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几度彷徨(改革+爱情,蓝色文学,寻根热;王安忆,张贤亮)面前,扎西达娃显得更为自觉、更为清醒一些;对于某些“容易满足”、“缺乏向更高目标追求精神的作家”(如张辛欣、北岛)说来,扎则显得更为老辣、沉稳和趋于大手笔。 1985—1986年是扎西达娃小说创作实现强突破之后进入全面整饬和酝酿新跃进的过渡期(当然,这种过渡是令人焦灼的)。过去的一年,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殊荣(《在甜茶馆里》获南方文学奖;《巴桑和她的弟妹们》载《收获》,被重庆电视台搬上银幕,并获全国电视剧独幕剧唯一的一等奖,作者出现剧中被评论界认为作家介入影视世界的新尝试;两个《西藏》(1)被评论界誉为“开放在西藏莽原上的魔幻现实主义之花”等),奠定了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有系列长篇《洛达镇轶事之一?自由人契米》的开放型结构和气度恢弘的时代背景,使读者始终处于拭目翘首的期待中。然而,作家这时说,“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也”,因此,“我企望悟出点什么。”(2)——是的,真有你的,好一个扎西达娃!
扎西达娃创作是以其“幽默”见长的。在当代的一些文艺作品中,似乎“幽默”可以直接与“浅薄”划等号。然而,“睿智与颖悟”才是“幽默”应有之义。扎西达娃的“幽默”正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的颖悟(或云顿悟),以其机敏睿智的艺术思辨为特征的。这,与严肃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构成作家作品基调。就创作方法而言,则表现为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下的文学创造(当然,这里的“幽默”则更富于一种发人颤栗的冷隽意味了)。
纵观作家作品,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统率着每一件创作。作家的话,道出了作家创作的真谛,是作家的自况,同时也为笔者蹩脚的探索揭橥了一条明晰的路。
现在,还是让我们从作家作品中得到证明。
首先,从作品的立意看——
《归途小夜曲》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偶然结合,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现实与神话、当代文明与传统因袭之间矛盾冲突的理性内容;《没有星光的夜》从阿格布化敌为友的心灵决斗中折射出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曦光,标识出历史的不可逆转;《江那边》、《谜样的黄昏》,作品文目本身就极富于哲理性;《宠儿》,两个新生儿的阴阳差错的襁褓易位,反映出后天社会对于先天血统关系的特定制约;《巴桑和她的弟妹们》中的“小哲学家”米玛,未始不是作家文本构思的一个哲学信符;《自由人契米》中的警察业务:有手铐而无脚镣;两个《西藏》中,于浓重的烟霭氤氲的宗教氛围笼罩下的关于民族意志走向的思考……
设若,就作家作品中的某一件投入思考,那么我们的结论也许是过于武断或失之狷狂;假使读者将作家的一系列作品联系起来考察,则这种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就显得十分灼母而又是如此咄咄警人的了。
其次,就作品的形象说——
A、人物形象
梅朵与姐姐琼姬(《在甜茶馆里》)走的是两条不同的人生之路。妹妹以甜茶馆生意劳动为生,姐姐爱慕虚荣寄生于一位商人浪荡子颔下。如此极富于理性思辨色彩的“背面敷粉法”(金圣叹)兹不赘述,而她们都摆脱不了时代社会和传统道德的牵系,或多或少地尽孝于“妈妈”膝前。勤劳、诚实、善良地梅朵也终逃不脱时尚习俗的侵扰——四月十五号同学的婚礼中的青春遭遇。
契米(《自由人契米》)八次入狱,八次越狱,如此逃犯,他的手竟然如此“奇异精美”,是“本来很适合在寺庙里擦祭器、铜像什么的”手;洛达镇警察“像在苦苦思索自己生活中这一辈子也没有解开的什么谜”。
巴桑(《巴桑和她的弟妹们》),这位母亲般的姐姐,操持着一个六口之家(爸爸、达娃、米玛、普布、尼玛),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与欢娱(三年未玩过一次林卡),与男朋友庶几持刀相向,面临着将要降临的婚姻,她的意见是:“他……真可怜。”
妮妮(《归途小夜曲》),乡间处子,落魄于一辆夜行货车,她极力抗拒青年司机的求爱,使出了“俄尔朵”鞭打的无情疯狂,然而,一段旅程之后,终于倒进对方的怀抱……
益西(《冥》),一个老妪。当年是“全西藏没有第二个的美人儿”,年轻时被加措抢来,几十年刀来枪往,晚年终于“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但,她念念不忘的仍是以前的“少爷”——今天在大昭寺门口看见的“那个人”……
信徒琼(《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抛弃爸爸和家庭矮房,追随苦修者塔贝,长途跋涉一百零八天,“走在解脱苦难终结的道路上”,直至塔贝于“莲花生掌纹地带”庄严(抑或荒唐?)献身,才结束她的穷途追索……
“文学即人学”(高尔基语)。如果文学,尤其是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体现其价值,那么“人”则是文学创作永远年轻的“座上宾”—因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 )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去发现、去探索人生要义乃至社会与人生、历史与人生、地理与人生……的哲理内容,则更为难能可贵。
B、意境形象
扎西达娃小说重在描写,诸如人物描写、情节描写、环境描写,却很少(几乎没有)动用意境描写,而他的意境形象是通过如上各种描写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作家似乎不屑于局部之处的意境处理,而着意于宏观把握方面的总体意境氛围创造。比如《归途》写当代爱情中的一对儿,作者将他们的“悲欢离合”放在茫茫草原雪夜、藏历年夕来写,大山、篝火、加油站、迪斯科、亚当、夏娃、伊甸园……通过如此一系列客体世界具象物的描写或某种信号展示,渠成水到地创造出“田园诗”和“牧歌式”的抒情意境来。1加1大于2,这里读者的审美凝注心理所接收的已不再是小说人物本身、故事情节本体、环境物象原貌所提供出来的有限信息,而是你由此构建起来、辐射出来的具有强烈哲学意味的无限内容,从而丰腴作品,使之步出二、三流小说之群,实现其价值。
诚然,出于作家的宏观审视效应,有时,也于有意无意之间构成某种意境:
门帘被缓缓地撩开一角。因为常年的油垢、污腻和烟熏,变得沉甸甸的,像一床脏乱不堪的羊毛被。外面的风溜进屋里四处回旋。矮桌上两只蜡烛的火苗被刮得动摇西晃,映在墙壁、屋顶上的投影也动了起来,忽大忽小,变得奇形怪状。
只有柜子上供在神像前的那盏豆大的酥油灯花始终保持不变的火苗,凝固似的纹丝不动,世尘空气的流动在它面前失去了活力。它显得肃穆、宁静……
——《冥》
很显然,这是(室内)环境描写,然而这环境描写的象征意蕴本身就构成某种意境且不去管它,因为这不是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即使我们说,作家未雨而绸缪,以具体的物象概念包蕴着某种抽象的理性内容为下面的情节描写卖下“关子”,也许被认为是“超感觉”,倘或我们读完作品的最后一个字,看小说结束时的那一个“复章”——又一次(室内)环境描写,那么读者当不会感到惊奇:
烛光熄灭了。屋内静悄悄的,只有屋角柜子上菩萨像前的那盏豆大的酥油灯花依然闪烁着微亮的光,它凝固般地纹丝不动。
这样,作者运用首尾两次环境描写的复沓,当中溶入主体部分人物、故事、情节的描写与交代,从而拓宽读者的想象空间和联系思维领域,形成了意境;或者说,作家通过艺术联想思维的发散和哲学抽象思维的收敛,借助于环境描写,勾勒出一个深邃浑凝的意境来。
再次,于表现手法讲——
A、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扎西达娃创作是以其“幽默”见长的。科诨而不失庄重,诙谐而不失严肃。亲情趣而理智,昵浪漫而现实,两者间的辩证统一,是扎的文学创造之于强烈哲学器识观照下的又一证明。
作家在写一对青年人的爱情时,是这样表现的:
罗珠(《归途》)向妮妮求爱,先炫耀自己一番,继而引导对方唱流行歌曲……最后终于抑制不住爱的 ,趁汽车颠簸的地赐良机给姑娘一个准确而实在的吻,此不禁让人哑然失笑;然静心思之,此不正是当代青年求爱的一种时髦方式么(当然艺术是夸张)?作为被爱得一方——妮妮又怎能坚守得住传统观念的堤防呢?
如此幽默,在作家作品中可谓俯拾即是。
契米(《自由人契米》)玩忽职守,草场大火,洛达镇人不予应有处罚,而寻出个“困惑不解的远方流浪人”作替罪羊,排着队伍,唱着歌,高高兴兴地喊着“一、二、三”,将其丢入玛曲河畔,此令人捧腹;然而掩卷思索,民族地域观念的传统负荷及愚氓意识又是何等沉重?
加措(《冥》)老爹的“屋中央方形木柱上”留下三十八条长短不齐的刀刻痕迹——他在这里“住了……三十……嘿,八,八年了。”而今,一道新痕刻下:
他捂着腰,一手撑着柱子直起身,吁了两声,像是欣赏杰作似的歪起头看了半天。似乎不满意,重新勾下身把那一道再拉长,一直拉到了柱子的边缘。再看看上面的那些歪歪斜斜的旧痕,都短得那么可怜,唯独刚才这道长长的新痕一下使他感到惊恐不安,像标志着某种物质的极限——
生命!
够了。扎西达娃凭着艺术家的机敏,擅于运用“幽默”,并且在幽默的描写中随时穿插一些与小说主题情节相表里相掩映的趣谈乐事(如《自由人》中关于“木碗”的传说,《巴桑》中关于“妈妈”的佳话等),在此故不枚举。作家以其情趣盎然、意蕴丰足的幽默征服了众多读者,是作家成功的堂奥所在。王蒙说,“小说毕竟不是必读文件,不是操作须知,不是农药使用说明……人们读它首先是因为它有趣。”(4)而扎的小说仅仅是“幽默”之“趣”而已么?
B、如果说笔者的评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请看作者自白(注意,在作家作品中,作家深得小说之妙,是绝不使用直白、使用议论的。这里,仅是作者的一个漏笔,而且是在大片描写之中偶尔疏漏了的):
当夜幕降临,巴尔郭便由白天闹哄哄的商业气氛转入晚上一片嗡嗡诵经声额宗教气氛里。成百上千的善男信女拥上街道。摇经筒的,拈佛珠的,捧香火的,端酥油灯的人流像一支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洪水般地漫溢着巴尔郭。从楼顶望下去,这股缓缓蠕动的黑压压的人流像一个古老而冥顽的宗教的灵魂,默默地在流逝的岁月里漂游;默默地跟随者时代的变迁;又仿佛在默默地向这个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世界发出执拗的挑战。——《巴桑》
这里,作家持之一贯的慎而又慎的客观冷静描写,由于一时疏忽,岂不泄露了“天机”
C、作家的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随着创作的成熟显得越发强烈:即由创作实践本身从而进入创作方法论的探讨,在他的中篇力作《魂》中,作家简直控制不住自己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下的理性冲动,以第一人称“我”(这是作家作品中唯一的)直接介入作品,作出如下表白:
此时此刻,我才发现一个为时过晚的真理,我那些“可爱的弃儿”们原来都是被赋予了生命和意志的。我让塔贝和琼从编有号码的牛皮纸袋里走出来,显然是犯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为什么我至今还没有塑造出一个“新人”形象来?这更是一个错误,对人物的塑造完成后,他们的一举一动即成客观事实,如果有人责问我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还允许他们的存在,我将作何回答呢?
关于创作方法论的问题,实质上即作家本体意志问题,属于思想观念范畴,只是由于文明社会科学分工的细密才将其派生出来从事专门研究罢了。文学批评的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谁反对创作方法是作家艺术地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某种规律,某种原则。(5)是服从于作家的审美观照——包括哲学器识、知识架构、心理品质等的某种思维定势(尽管它在某个时期或某一部作品中可能发生变化)——即本体意志的。也就是说,作家采用什么方法,(笔者认为,无论什么方法乃至流派、主义,诸如意识流、黑色幽默、现代派、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反小说、荒诞、魔幻……都逃不出现实主义的如来佛掌。对艺术来说,除创作家外,只有以现实社会的客体存在为形式特征的人类世界才是永恒的),塑造什么形象,表现什么内容等等均由作家的本体意志来决定。“从喷泉里流出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鲁迅语)至于写“新人”、“旧人”,写落后人物、中间人物、先进人物乃至“高大全”式英雄模范人物,这是当代文学史上自五十年代以来纠缠不清久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是最没意义的问题。它除了让我们有幸熟睹了非常时代政治是如何强奸艺术的粗暴与狰狞,似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归根结蒂,关于创作方法论的问题实质是作家对于时代社会的审美观照孰器孰道的问题。
可不是?就在《魂》中,于小说结尾处,作者写道:
我代替了塔贝,琼跟在我后面,我们一起往回走。时间又从头算起。
“琼”不是“新人”,然而作者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揭橥了“琼”之尚且不能称之为“新人”的基因——甘(抑或不甘?)于自戕精神惰性因素,从而将“琼”从盲目膜拜顶礼于朝圣的迷途上挽回,踏入坚实的社会生活大地,随着时间巨人的步履走向前途……至此,落后于时代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由执迷而盲从直至醒觉,奕奕然出现于时代前进行列之中了! 共 6867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扎西达娃的每一个文学创造,无不置于作家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之下,表现出鲜明的本体意志色彩,呈现出一如既往的理性思维定势。作家始终不渝地朝着他既定的目标奋进。与当代文坛上的某些作家相比,在当代文学走向深入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几度彷徨面前,扎西达娃显得更为自觉、更为清醒一些;作者的第二篇关于扎西达娃的作品赏析。对这位少数民族作家的数部小说,做出了精细的分析,非常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他在这些作品中的天赋。作品论述精湛,逻辑严密,是出色的赏析作品。感谢成功梧桐文苑【编辑:江南铁鹰】
2 楼 文友: 2015-0 -2 21:11:11 拜读欣赏作品赏析,祝您春日吉祥,创作愉快!
楼 文友: 2015-0 -24 09:01:42 拜读、欣赏、学习中 云烟深处懒读书跌打损伤骨折吃什么好心脉痹阻证中成药治筋骨疼痛的中药材有哪些
扎西达娃创作是以其“幽默”见长的。在当代的一些文艺作品中,似乎“幽默”可以直接与“浅薄”划等号。然而,“睿智与颖悟”才是“幽默”应有之义。扎西达娃的“幽默”正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的颖悟(或云顿悟),以其机敏睿智的艺术思辨为特征的。这,与严肃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构成作家作品基调。就创作方法而言,则表现为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下的文学创造(当然,这里的“幽默”则更富于一种发人颤栗的冷隽意味了)。
纵观作家作品,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统率着每一件创作。作家的话,道出了作家创作的真谛,是作家的自况,同时也为笔者蹩脚的探索揭橥了一条明晰的路。
现在,还是让我们从作家作品中得到证明。
首先,从作品的立意看——
《归途小夜曲》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偶然结合,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现实与神话、当代文明与传统因袭之间矛盾冲突的理性内容;《没有星光的夜》从阿格布化敌为友的心灵决斗中折射出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曦光,标识出历史的不可逆转;《江那边》、《谜样的黄昏》,作品文目本身就极富于哲理性;《宠儿》,两个新生儿的阴阳差错的襁褓易位,反映出后天社会对于先天血统关系的特定制约;《巴桑和她的弟妹们》中的“小哲学家”米玛,未始不是作家文本构思的一个哲学信符;《自由人契米》中的警察业务:有手铐而无脚镣;两个《西藏》中,于浓重的烟霭氤氲的宗教氛围笼罩下的关于民族意志走向的思考……
设若,就作家作品中的某一件投入思考,那么我们的结论也许是过于武断或失之狷狂;假使读者将作家的一系列作品联系起来考察,则这种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就显得十分灼母而又是如此咄咄警人的了。
其次,就作品的形象说——
A、人物形象
梅朵与姐姐琼姬(《在甜茶馆里》)走的是两条不同的人生之路。妹妹以甜茶馆生意劳动为生,姐姐爱慕虚荣寄生于一位商人浪荡子颔下。如此极富于理性思辨色彩的“背面敷粉法”(金圣叹)兹不赘述,而她们都摆脱不了时代社会和传统道德的牵系,或多或少地尽孝于“妈妈”膝前。勤劳、诚实、善良地梅朵也终逃不脱时尚习俗的侵扰——四月十五号同学的婚礼中的青春遭遇。
契米(《自由人契米》)八次入狱,八次越狱,如此逃犯,他的手竟然如此“奇异精美”,是“本来很适合在寺庙里擦祭器、铜像什么的”手;洛达镇警察“像在苦苦思索自己生活中这一辈子也没有解开的什么谜”。
巴桑(《巴桑和她的弟妹们》),这位母亲般的姐姐,操持着一个六口之家(爸爸、达娃、米玛、普布、尼玛),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与欢娱(三年未玩过一次林卡),与男朋友庶几持刀相向,面临着将要降临的婚姻,她的意见是:“他……真可怜。”
妮妮(《归途小夜曲》),乡间处子,落魄于一辆夜行货车,她极力抗拒青年司机的求爱,使出了“俄尔朵”鞭打的无情疯狂,然而,一段旅程之后,终于倒进对方的怀抱……
益西(《冥》),一个老妪。当年是“全西藏没有第二个的美人儿”,年轻时被加措抢来,几十年刀来枪往,晚年终于“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但,她念念不忘的仍是以前的“少爷”——今天在大昭寺门口看见的“那个人”……
信徒琼(《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抛弃爸爸和家庭矮房,追随苦修者塔贝,长途跋涉一百零八天,“走在解脱苦难终结的道路上”,直至塔贝于“莲花生掌纹地带”庄严(抑或荒唐?)献身,才结束她的穷途追索……
“文学即人学”(高尔基语)。如果文学,尤其是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体现其价值,那么“人”则是文学创作永远年轻的“座上宾”—因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 )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去发现、去探索人生要义乃至社会与人生、历史与人生、地理与人生……的哲理内容,则更为难能可贵。
B、意境形象
扎西达娃小说重在描写,诸如人物描写、情节描写、环境描写,却很少(几乎没有)动用意境描写,而他的意境形象是通过如上各种描写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作家似乎不屑于局部之处的意境处理,而着意于宏观把握方面的总体意境氛围创造。比如《归途》写当代爱情中的一对儿,作者将他们的“悲欢离合”放在茫茫草原雪夜、藏历年夕来写,大山、篝火、加油站、迪斯科、亚当、夏娃、伊甸园……通过如此一系列客体世界具象物的描写或某种信号展示,渠成水到地创造出“田园诗”和“牧歌式”的抒情意境来。1加1大于2,这里读者的审美凝注心理所接收的已不再是小说人物本身、故事情节本体、环境物象原貌所提供出来的有限信息,而是你由此构建起来、辐射出来的具有强烈哲学意味的无限内容,从而丰腴作品,使之步出二、三流小说之群,实现其价值。
诚然,出于作家的宏观审视效应,有时,也于有意无意之间构成某种意境:
门帘被缓缓地撩开一角。因为常年的油垢、污腻和烟熏,变得沉甸甸的,像一床脏乱不堪的羊毛被。外面的风溜进屋里四处回旋。矮桌上两只蜡烛的火苗被刮得动摇西晃,映在墙壁、屋顶上的投影也动了起来,忽大忽小,变得奇形怪状。
只有柜子上供在神像前的那盏豆大的酥油灯花始终保持不变的火苗,凝固似的纹丝不动,世尘空气的流动在它面前失去了活力。它显得肃穆、宁静……
——《冥》
很显然,这是(室内)环境描写,然而这环境描写的象征意蕴本身就构成某种意境且不去管它,因为这不是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即使我们说,作家未雨而绸缪,以具体的物象概念包蕴着某种抽象的理性内容为下面的情节描写卖下“关子”,也许被认为是“超感觉”,倘或我们读完作品的最后一个字,看小说结束时的那一个“复章”——又一次(室内)环境描写,那么读者当不会感到惊奇:
烛光熄灭了。屋内静悄悄的,只有屋角柜子上菩萨像前的那盏豆大的酥油灯花依然闪烁着微亮的光,它凝固般地纹丝不动。
这样,作者运用首尾两次环境描写的复沓,当中溶入主体部分人物、故事、情节的描写与交代,从而拓宽读者的想象空间和联系思维领域,形成了意境;或者说,作家通过艺术联想思维的发散和哲学抽象思维的收敛,借助于环境描写,勾勒出一个深邃浑凝的意境来。
再次,于表现手法讲——
A、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扎西达娃创作是以其“幽默”见长的。科诨而不失庄重,诙谐而不失严肃。亲情趣而理智,昵浪漫而现实,两者间的辩证统一,是扎的文学创造之于强烈哲学器识观照下的又一证明。
作家在写一对青年人的爱情时,是这样表现的:
罗珠(《归途》)向妮妮求爱,先炫耀自己一番,继而引导对方唱流行歌曲……最后终于抑制不住爱的 ,趁汽车颠簸的地赐良机给姑娘一个准确而实在的吻,此不禁让人哑然失笑;然静心思之,此不正是当代青年求爱的一种时髦方式么(当然艺术是夸张)?作为被爱得一方——妮妮又怎能坚守得住传统观念的堤防呢?
如此幽默,在作家作品中可谓俯拾即是。
契米(《自由人契米》)玩忽职守,草场大火,洛达镇人不予应有处罚,而寻出个“困惑不解的远方流浪人”作替罪羊,排着队伍,唱着歌,高高兴兴地喊着“一、二、三”,将其丢入玛曲河畔,此令人捧腹;然而掩卷思索,民族地域观念的传统负荷及愚氓意识又是何等沉重?
加措(《冥》)老爹的“屋中央方形木柱上”留下三十八条长短不齐的刀刻痕迹——他在这里“住了……三十……嘿,八,八年了。”而今,一道新痕刻下:
他捂着腰,一手撑着柱子直起身,吁了两声,像是欣赏杰作似的歪起头看了半天。似乎不满意,重新勾下身把那一道再拉长,一直拉到了柱子的边缘。再看看上面的那些歪歪斜斜的旧痕,都短得那么可怜,唯独刚才这道长长的新痕一下使他感到惊恐不安,像标志着某种物质的极限——
生命!
够了。扎西达娃凭着艺术家的机敏,擅于运用“幽默”,并且在幽默的描写中随时穿插一些与小说主题情节相表里相掩映的趣谈乐事(如《自由人》中关于“木碗”的传说,《巴桑》中关于“妈妈”的佳话等),在此故不枚举。作家以其情趣盎然、意蕴丰足的幽默征服了众多读者,是作家成功的堂奥所在。王蒙说,“小说毕竟不是必读文件,不是操作须知,不是农药使用说明……人们读它首先是因为它有趣。”(4)而扎的小说仅仅是“幽默”之“趣”而已么?
B、如果说笔者的评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请看作者自白(注意,在作家作品中,作家深得小说之妙,是绝不使用直白、使用议论的。这里,仅是作者的一个漏笔,而且是在大片描写之中偶尔疏漏了的):
当夜幕降临,巴尔郭便由白天闹哄哄的商业气氛转入晚上一片嗡嗡诵经声额宗教气氛里。成百上千的善男信女拥上街道。摇经筒的,拈佛珠的,捧香火的,端酥油灯的人流像一支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洪水般地漫溢着巴尔郭。从楼顶望下去,这股缓缓蠕动的黑压压的人流像一个古老而冥顽的宗教的灵魂,默默地在流逝的岁月里漂游;默默地跟随者时代的变迁;又仿佛在默默地向这个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世界发出执拗的挑战。——《巴桑》
这里,作家持之一贯的慎而又慎的客观冷静描写,由于一时疏忽,岂不泄露了“天机”
C、作家的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随着创作的成熟显得越发强烈:即由创作实践本身从而进入创作方法论的探讨,在他的中篇力作《魂》中,作家简直控制不住自己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下的理性冲动,以第一人称“我”(这是作家作品中唯一的)直接介入作品,作出如下表白:
此时此刻,我才发现一个为时过晚的真理,我那些“可爱的弃儿”们原来都是被赋予了生命和意志的。我让塔贝和琼从编有号码的牛皮纸袋里走出来,显然是犯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为什么我至今还没有塑造出一个“新人”形象来?这更是一个错误,对人物的塑造完成后,他们的一举一动即成客观事实,如果有人责问我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还允许他们的存在,我将作何回答呢?
关于创作方法论的问题,实质上即作家本体意志问题,属于思想观念范畴,只是由于文明社会科学分工的细密才将其派生出来从事专门研究罢了。文学批评的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谁反对创作方法是作家艺术地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某种规律,某种原则。(5)是服从于作家的审美观照——包括哲学器识、知识架构、心理品质等的某种思维定势(尽管它在某个时期或某一部作品中可能发生变化)——即本体意志的。也就是说,作家采用什么方法,(笔者认为,无论什么方法乃至流派、主义,诸如意识流、黑色幽默、现代派、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反小说、荒诞、魔幻……都逃不出现实主义的如来佛掌。对艺术来说,除创作家外,只有以现实社会的客体存在为形式特征的人类世界才是永恒的),塑造什么形象,表现什么内容等等均由作家的本体意志来决定。“从喷泉里流出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鲁迅语)至于写“新人”、“旧人”,写落后人物、中间人物、先进人物乃至“高大全”式英雄模范人物,这是当代文学史上自五十年代以来纠缠不清久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是最没意义的问题。它除了让我们有幸熟睹了非常时代政治是如何强奸艺术的粗暴与狰狞,似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归根结蒂,关于创作方法论的问题实质是作家对于时代社会的审美观照孰器孰道的问题。
可不是?就在《魂》中,于小说结尾处,作者写道:
我代替了塔贝,琼跟在我后面,我们一起往回走。时间又从头算起。
“琼”不是“新人”,然而作者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揭橥了“琼”之尚且不能称之为“新人”的基因——甘(抑或不甘?)于自戕精神惰性因素,从而将“琼”从盲目膜拜顶礼于朝圣的迷途上挽回,踏入坚实的社会生活大地,随着时间巨人的步履走向前途……至此,落后于时代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由执迷而盲从直至醒觉,奕奕然出现于时代前进行列之中了! 共 6867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扎西达娃的每一个文学创造,无不置于作家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之下,表现出鲜明的本体意志色彩,呈现出一如既往的理性思维定势。作家始终不渝地朝着他既定的目标奋进。与当代文坛上的某些作家相比,在当代文学走向深入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几度彷徨面前,扎西达娃显得更为自觉、更为清醒一些;作者的第二篇关于扎西达娃的作品赏析。对这位少数民族作家的数部小说,做出了精细的分析,非常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他在这些作品中的天赋。作品论述精湛,逻辑严密,是出色的赏析作品。感谢成功梧桐文苑【编辑:江南铁鹰】
2 楼 文友: 2015-0 -2 21:11:11 拜读欣赏作品赏析,祝您春日吉祥,创作愉快!
楼 文友: 2015-0 -24 09:01:42 拜读、欣赏、学习中 云烟深处懒读书跌打损伤骨折吃什么好心脉痹阻证中成药治筋骨疼痛的中药材有哪些
最近更新小说列表
- 09-07[都市]看考场不是走过场,2022中考考场踩点注记,踩点前必看!
- 07-11[都市]堪比好莱坞大片,看老黄如何运用三十六计,破2022高考数学分析的堡垒
- 07-09[都市]卧室不安装双人床,而是直接在地面三脚"它",省空间显宽敞
- 06-25[都市]在一起贵了你就会发现 他不仅会骂你 烦你 还会盖起被子继续睡 不管你哭成什么样都不会哄你 只会觉得你
- 06-22[都市]你们都喜欢网红楼梯!我太太踩的坑你们可要避开!最后有整个楼梯的清单,给你们参考!网红楼梯 魅族lip
- 06-21[都市]“失联”近半年,董卿丈夫有了新消息!明天起正常履职董事长!去年财富超100亿,如今旗下上市公司即将开
- 06-08[都市]直击调研 | 中材科技(002080.SZ):今年叶片出货量预计同比增加20% 十四五末期膜产能或达
- 06-06[都市]Ulster霍尔大学优质课程推荐 BSc Nursing Science (Top-up) & MS
- 06-05[都市]Ulster霍尔大学优质课程推荐 BSc Nursing Science (Top-up) & MS
- 05-13[都市]九分裤+乐福鞋,夏日这样穿,时髦又显高,很适合小个子
- 04-22[都市]虐心,兔子彻底被机械化,红红好不容易才想起以前事情,拍视频怕忘记大家就决战次时代 雀跃 多想留在你身
- 04-06[都市]海洋水质的网站监测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 04-03[都市]哪有什么真直男 都是装直男 他发觉你生气了 需要哄 也发觉消息要及时回 也发觉要关心你 给你买喜欢的